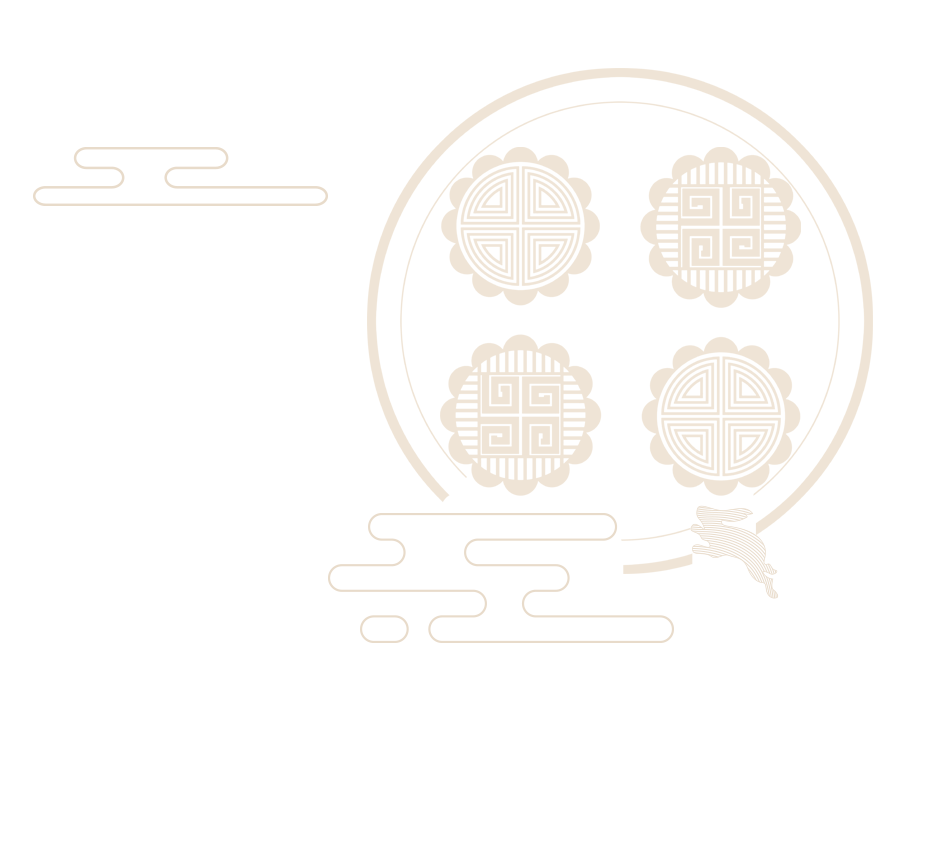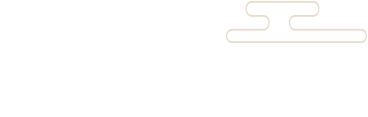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金華是個包容的城市】
金華自古尚禮。傳說早在宋時,每逢中秋,永康一帶就有畫餅祭月神的習俗。古婺大地不長麥子,卻是魚米之鄉(xiāng)。古婺先民就將米粉蒸熟,眾人合力搟出個一人多高的白色圓餅,豎立供于堂前。隨后即有族中長者在上面畫上族人的美好祈愿。幾番祭拜之后,大圓餅被切開,族中人悉數(shù)分食,接受賜福。禮俗不再,故事里的“畫餅”經現(xiàn)代化改良,成了紅遍金華市民微信朋友圈的“婺式”月餅,五仁餡兒、芝麻餡兒、火腿餡兒、巧克力餡兒……各種口味應有盡有。婺城區(qū)新一代非遺傳承人徐家興還通過淘寶等渠道將它推向了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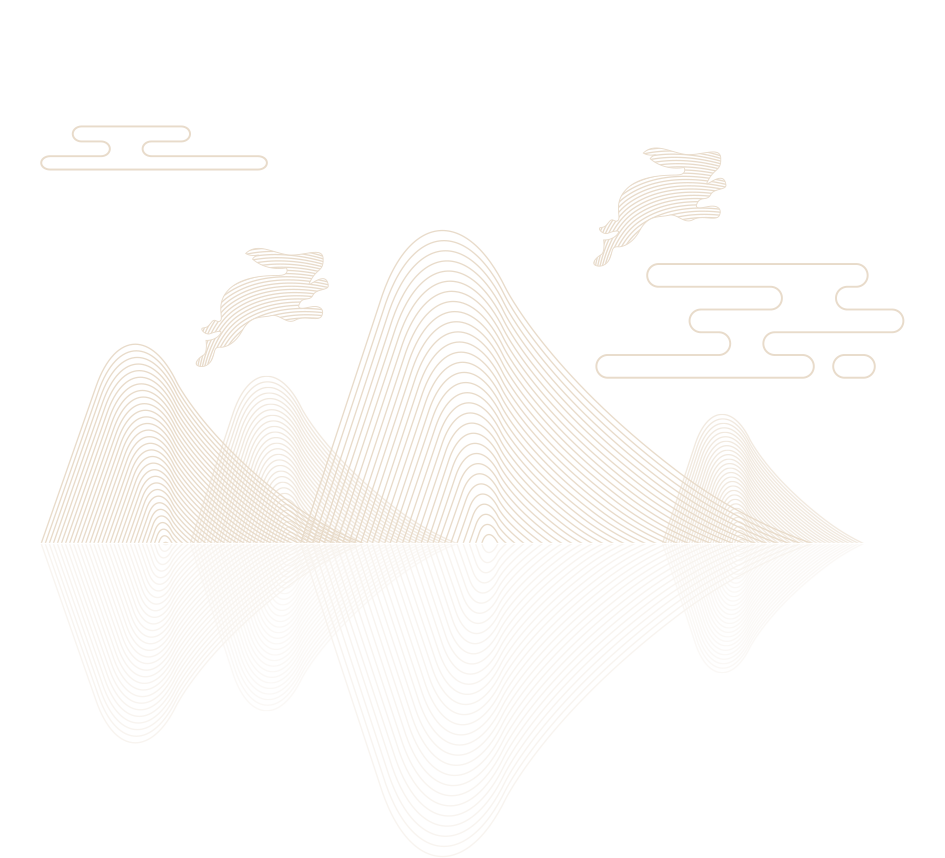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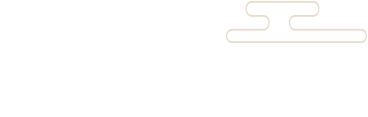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故鄉(xiāng)仿佛成了他鄉(xiāng),他鄉(xiāng)卻在不經意間成了故鄉(xiāng)】
這座曾經與她毫無瓜葛的城市,留下了太多她此生都無法割舍的東西。她在這里初探社會,結交摯友,安了小窩,遇見愛人,如今又有了可愛的小女兒。這座城市承載了她人生最重要的內容。如今,王慧只愿在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守護女兒小愛心健康快樂地長大。女兒在哪兒,家就在哪兒。她要陪伴她過每一個圓滿的中秋節(ji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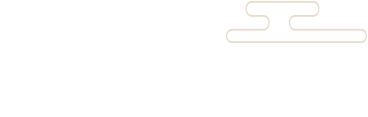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也在這里有了放不下的牽掛】
佛山是故鄉(xiāng),金華是家鄉(xiāng)。無論身在何處,心頭的鄉(xiāng)愁總是揮之不去。他久居金華,卻總在卯足了勁兒地尋找“廣東味”,到澳門十五茶餐廳點名讓老板開小灶做清蒸的鱸魚,到一百二樓吃正宗的粵式腸粉……每年的清明,他堅持攜妻子回到佛山,虔誠祭掃,卻終究還是選擇回到金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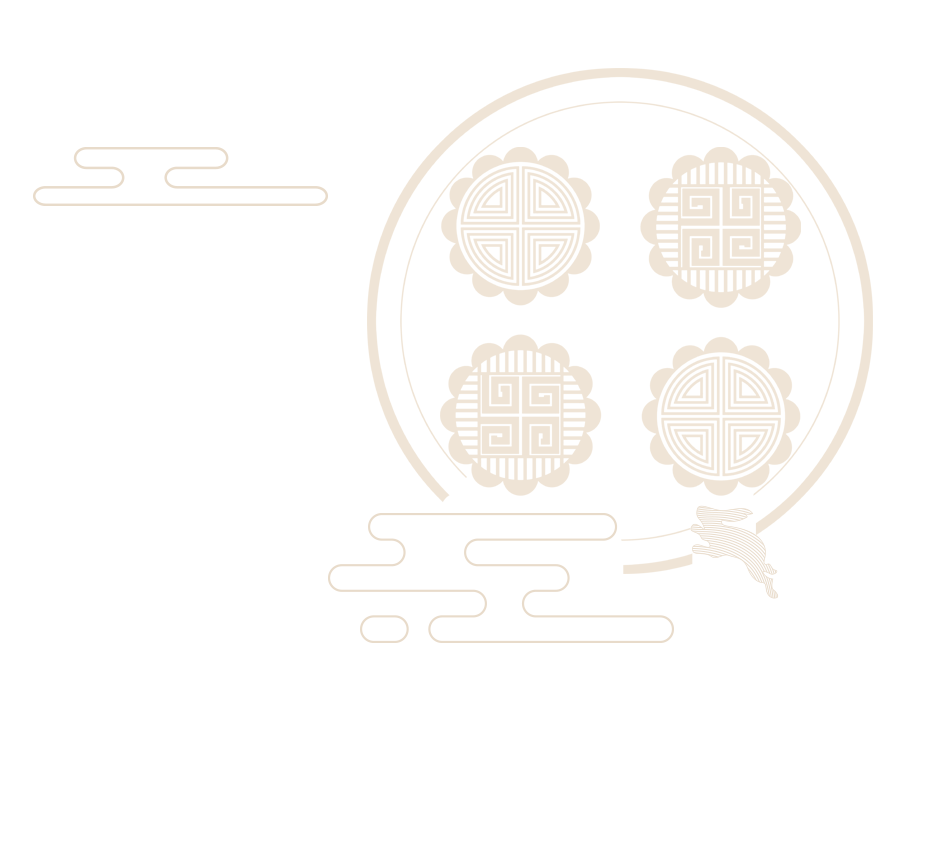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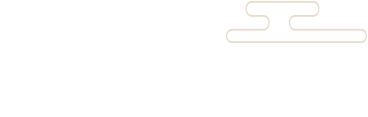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她選擇守護在金華的小團圓】
每逢中秋,重慶總有厚皮果脯餡兒的傳統(tǒng)京式月餅,但最讓李秀花垂涎的還是街上賣的“冰薄月餅”。這種月餅沒有餡兒,所有甜蜜都被拌進面里,搟成薄薄的一層,上面撒滿了白色的芝麻,放進爐里烤得噴香,然后一張疊著一張累成一大摞,被街坊鄰居一圓筒一圓筒地提回家去。然而,小時候,除了這口好吃的,李秀花是個“過節(jié)盲”,對故鄉(xiāng)的中秋并沒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因為“那時候一家人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是團圓節(ji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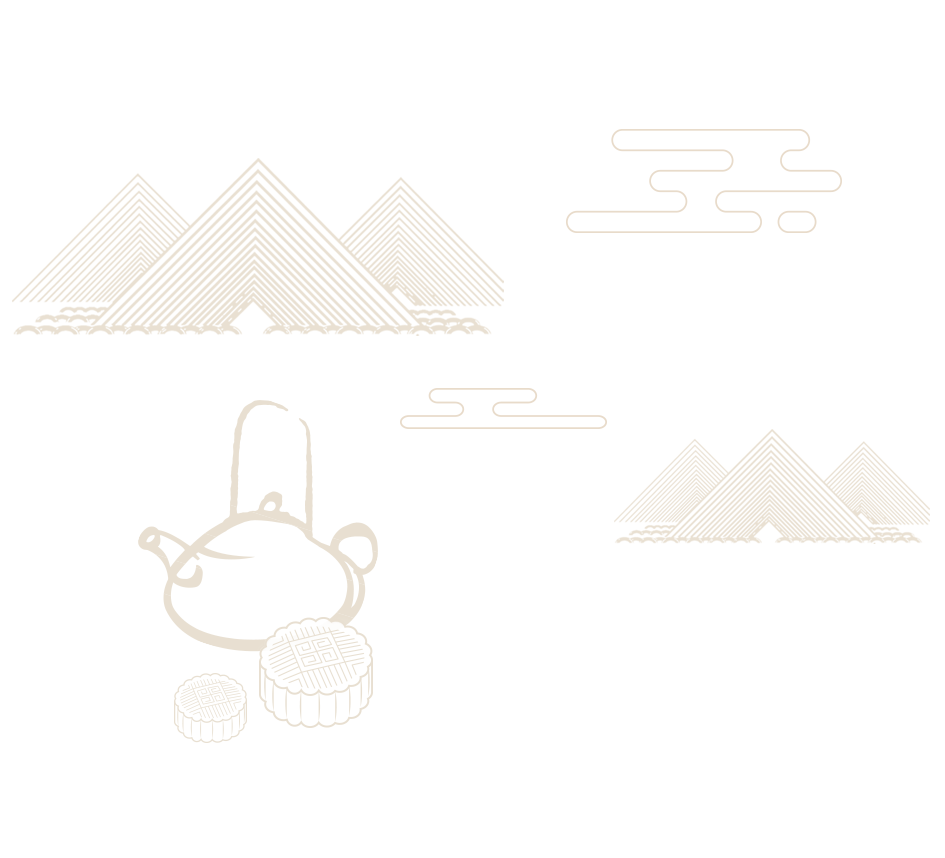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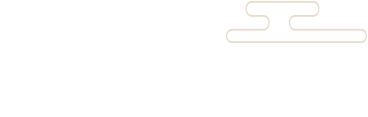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這個洞庭湖畔的小家庭在婺江相聚】
張必強和妻子都是湖南岳陽人,說起老家的中秋節(jié),夫妻倆相視一笑,拿手比劃著:“我們老家的月餅都這么大。”每到中秋,全家人圍在一起,像切蛋糕一樣切開大如臉盆的月餅,里頭餡兒是冰糖、紅棗、花生。然后,再趕往外婆家,和舅舅、阿姨一家吃著外婆做的家常菜。飯后,是過年過節(jié)里固定不變的娛樂項目“歪胡子”紙牌,不在乎贏輸,重要的是兄弟姐妹間打著趣兒互相“吐槽”。“其實我感覺我們老家的中秋習俗和婺城這邊的也沒差太多。”應必強思索著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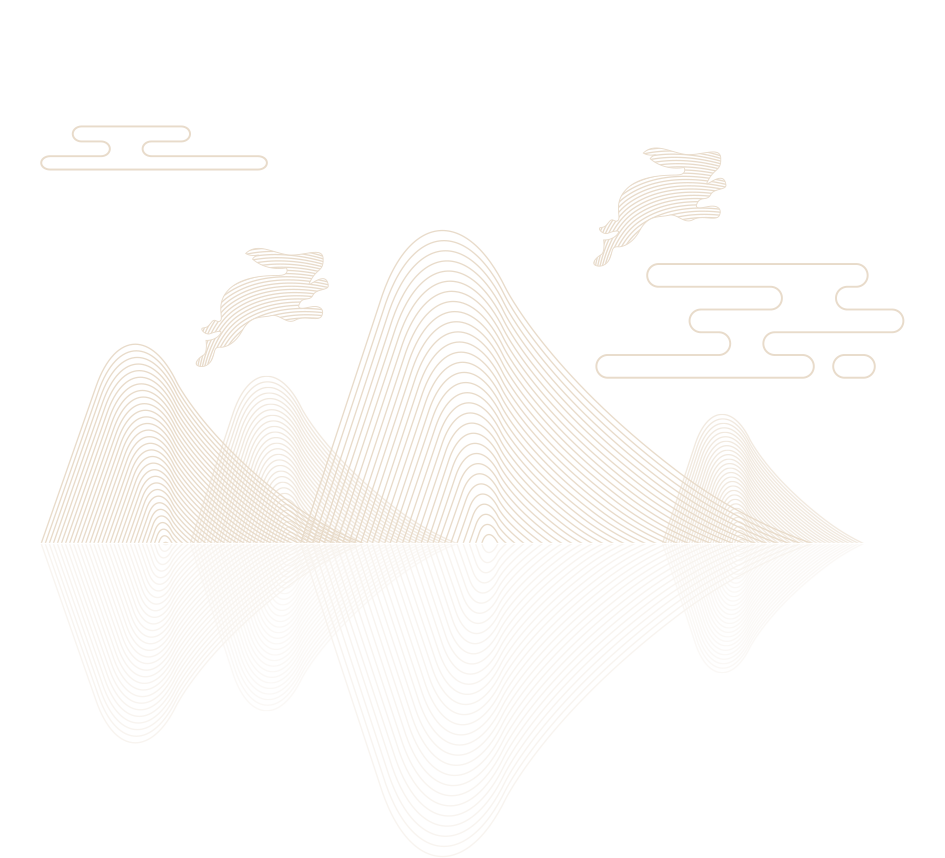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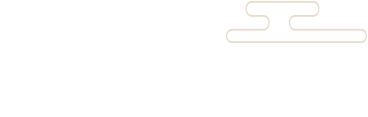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婺城儼然成了他的第二故里】
張述章是福建沙縣人。在他兒時的計劃經濟時代,每年的中秋,家里人很多,也很齊,吃食卻很少。這一天,但凡父母健在,出嫁的女兒必當攜丈夫孩子一起提著月餅回娘家團圓。家鄉(xiāng)的月餅很大,有足足八寸,兩個就能裝一提,月餅用土黃色的紙包著,用稻草繩系著,古色古香。月餅外面撒著芝麻,里面包著紅糖。一個大月餅,掰開了一家人分著吃。家里有兄弟姐妹六個,長輩們總說不愛吃,讓小孩子們多吃一點。父親雖是個農民,得了空總愛刻刻畫畫,中秋月下,他總在給村人制印,偶爾也玩玩木雕。后來,改革開放,村里人一波接著一波往外跑,極少有回來的,他就在想,或許,別處還有個故鄉(xiā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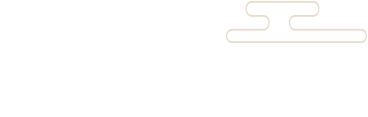
【共話故里風俗事,新朋似舊友】
在金華職業(yè)技術學院的西操場上,耀眼的迷彩服在陽光下開成一簇簇的綠色軍花。這屆大一新生多在1998年和1999年出生。最后一批“90后”已悄然開始了他們的大學生活。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將在這里過第一個不能與家人團聚的中秋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