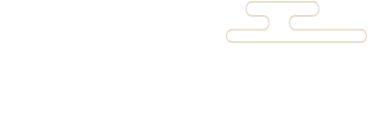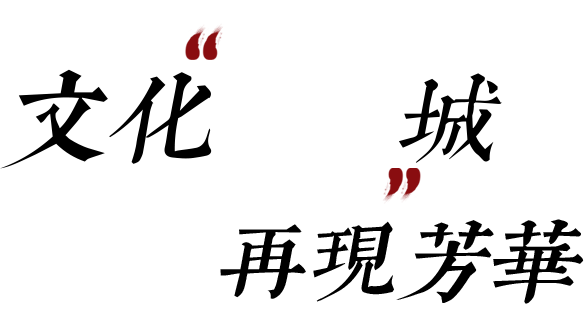【承載了金華城的古今水運變遷】
這里曾是李清照避難時踏上的江渚,徐霞客深夜造訪的港灣,黃賓虹迸發藝術靈感的街巷,這里承載了金華人最地道的古城記憶,最淳樸的煙火日常。金華小碼頭,一個牽動無數人思緒的地方。何孫耕,這位96歲的老人,從民國走到新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到改革開放,從事金華地區、金華縣多項重大水利、教育、農業項目規劃與建設,于時光洪流中暮然回首,細說著金華小碼頭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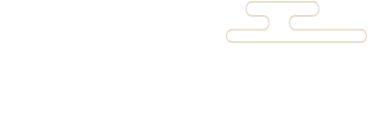
【一座城池,多少王超興衰史】
古子城、水門巷、鼓樓里……古城遺跡如行游江渚的白發漁樵,任時光拂面,烙印下皺紋,笑看風雨。東漢設縣,三國分郡,隋代建州。婺城的故事,從一座圍城開始。城門外沙塵浩浩,城樓上狼煙滾滾,幾經戰亂風雨,幾度時代更迭。圍城屢毀屢建,仿若秋去春來。歷史畫卷里,有人讓位求和,有人舍身取義,有人碌碌一生,有人名垂青史。呂學姜,一位幼時生活在婺州古城長仙門附近的78歲老人,回顧兒時記憶,細數坊間傳說,描畫著這片土地上的古舊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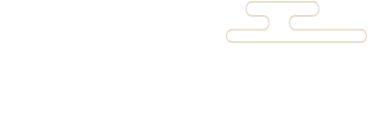
【“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昔年為客處,今日送君游。”】
婺城三大名樓,始建于不同年代,以其驚世氣度,引來達官顯貴相攜登臨,文人墨客爭相題詠,卻最終走向了三種迥然不同的命運,在婺州古城文化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時至今日,婺州古城滄海桑田,八詠樓卻是金星、婺女爭輝之下屹立不倒的傳奇。“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昔年為客處,今日送君游。”時光機倒流到唐代,一日,詩人嚴維送別友人到金華旅游,想起那是自己曾經去過的地方,便做起了景點推薦,卻出乎意料地預言了婺城三大名樓的卓越風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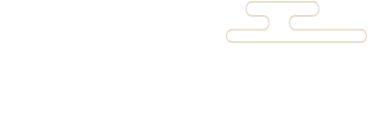
【“四眼”“蓮花”話日常】
“繁華市井”、“背井離鄉”、“飲水不忘挖井人”……從基本的生活所需到心頭的故鄉情思,水井之于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在婺城,水井遍布屋后街角,更有有富、貴、貧、賤之分。四眼井水量充沛,附近居民挑水磨豆腐,賣錢致富,是富井。蓮花井旁貴人名士圍井而居,是貴井。鐵嶺頭背上雙眼井天旱即涸,是貧井。攔路井在鬧市街被千人踏、萬人跨,是賤井。等第鮮明的婺城古井蘸滿了人間煙火,讓人嗅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更似一頁頁剪影,展現著婺城先民尋找生命水源的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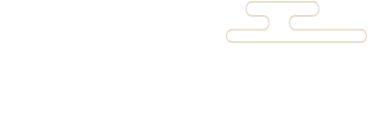
【婺城老街巷里“聽”故事 】
歲月如水,滌去歷史煙塵。然而,中華民族的精神,安逸小城的擔當,卻在古巷斑駁的舊影中,紅色故事里,代代傳承。旌孝街,這條因宋時有女聽信江湖醫囑,自剁一手救父的故事而得名的老街,鮮血早已流出了不同的意義。在其南端蓋起了軍分區干休所。迎著淺淺的秋意,九旬老兵曹海云翻開泛黃的影集,就著自己寫的回憶錄《戎馬生涯》,給兒孫們講述著他的抗戰經歷,這座城市、這個民族的滄桑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