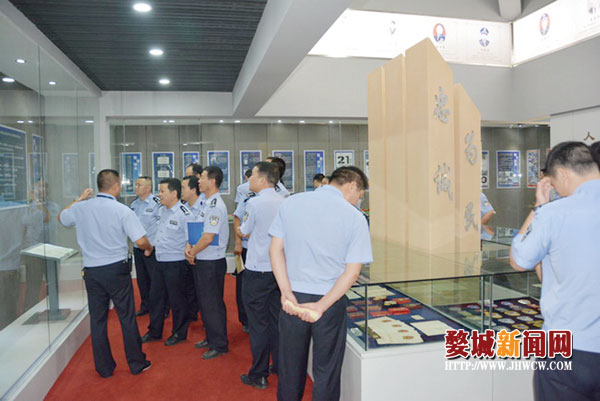洞叭塢是金華湯溪鎮去城南十五里左右的一個小山谷,多年以來,它鮮為外人所知,如今更是無人提及。
多年以前,我在其中割草、放牛、摘花,在林子里瘋跑,洞叭塢的春天是滿山遍野的杜鵑。那些深紅色的、粉紅色的、淺紫的、粉白的,一簇簇一團團,擁擠在一起,爭先恐后地涌來。她們的笑臉都那么燦爛,你分不清到底誰是誰,哪一朵更美,她們環繞在你的腳邊,環繞在你前面、后面、左邊、右邊,你抬頭看也是,低頭看也是,膽小的含羞斂眉,膽大的站在高坡,迎風怒放。她們吵吵嚷嚷的,細小的喉嚨里發出無數的叫喊,吵得整座山都沸騰起來。馬尾松們、黑松們、樟樹們、櫟樹們,腦袋都被吵大了、吵昏了,昏昏欲睡,春天嘛!春眠不覺曉嘛!但是他們微笑著,一言不發,忍受著這個寧靜世界的喧鬧。她們小小的花瓣那么單薄,又那么自然鮮艷,像這大山里扎著麻花辮、穿著花布衣、不施脂粉的鄉下妹子。有時候她們魚貫而行,高低錯落;有時候又擠成一團,你的胳膊伸到我的臉上,我的大腿叉到你的腰;有時候又規規矩矩地并排蹲著,蹲得低低的,兩張臉貼在一起,拘謹得好像鄉下妹子第一次上城照像。這滿目的花朵是大山胸膛里按捺不住的春意。仿佛從冬天開始,它們就開始蘊蓄,在骨頭里、血液里、心臟里,一點一點地增加暖意。太陽一天天高起來,它們凍僵的血脈天始流暢,它們的頭發生長得很快,身體不安起來、靈活起來。幾場春雨一下,春風一吹,蘊藏在體內的力量、欲望、喜悅、新奇和不安,像地底灼熱的熔巖,沖破皮膚、骨頭、心臟、毛細血管,一齊爆發出來,從山頂到山腳,流淌了一地。
從曹界村出發,到達洞叭塢,必須步行。出了村,走過一條窄窄的石坂橋,走上一條黑黝黝的泥土路,兩邊是大大小小的蔬菜地,通常種著包菜、萵筍、大蒜、蠶豆之類,都是些大路菜,全眼熟。這里的農民思想有點固執,幾乎一成不變地遵守著祖例,爺爺種什么、父親種什么,他就種什么。冬種麥、夏種稻、年前播蠶豆、過了谷雨插蕃暑,年年如此,不會想著去弄點西芹種種,弄點桂花樹種種,弄點玫瑰花種種。一方面是出類拔萃的東西容易遭賊,另一方面也是人心太平,貪安逸,守現成,不愿去動腦筋想門路。
沿著小路往前走,路高高低低不平,山的意思漸漸明顯。雖然不高,但已經是山了。途中碰到一條小澗,時而平緩地流著,時而從巖縫時嘩嘩地沖下來。那水是白色的、冰冷的、新鮮而充滿活力的,帶著草根和落葉的氣息。大約走三里多路,山勢時而分開時而合攏,漸漸匯集成一個峽口,寬不過三四十米,一路跟隨的小澗在不遠處急劇地高聲喧嘩。斑鳩叫起來了,翠綠色的小鳥在草叢中撲騰,又刷的一聲飛走。山更加沉默,馬尾松的陰影投在地上只有一小塊。一切都驚疑不定地等待著什么。你預感到什么要發生,什么要出現。但你不知道,即使處在一雙老虎的陰郁的眼光注視下你也不知道,路旁就伏著一只野豬你也沒察覺,整個世界看上去都無動于衷,好像都睡去了,只有太陽是活的,光線會走動,你感覺到有了一個伙伴,但它是漠不關心的。實際上當你在山間走動的時候,有多少雙眼睛在注視你,多少雙耳朵在傾聽:小鳥在樹枝上偏著頭打量;天空中飛旋的鷹在惴度你的個體;野兔在洞中驚魂未定,腦脯一起一伏;蛇和沙鰍感覺到你的腳步的震動,它們脆弱的小心臟沉受不住,紛紛在草叢中游走。當我們一個人在深山曠野里行走的時候,常常感覺身上發冷,害怕,實際上什么也沒有,你感覺到的是寂靜帶給你的威懾和壓力。山不長手不長腳,不會跳出來打你一拳,也不會突然變形成為一個魔鬼,但它那么沉默地坐著,一聲不吭,你唱歌它也不笑,你咒罵它也不回聲,拳打腳踢也沒用,它巨大的陰影一會兒就覆蓋了你,你感覺到頭發被染綠了,眼睛一片烏黑,除了山什么也看不見,你被山吞噬了,被寂靜吞噬了。
出了峽口,按理應該是“眼前一片豁然開朗”,像桃花源一樣。但不是。雖然寬了許多,山勢稍稍地退開了些,但仍是一條小路,沿山腳一條小溪,路邊是一小塊一小塊種著油菜或小麥的田。但是人頓時輕松了許多,沉重的壓迫感消失了,蜜蜂嗡嗡地叫著,油菜花這么香,遠處一片茶園隨著坡地起伏,一直延伸到山腰。正對著峽口的山峰苑如一只巨大的兔子,仰著頭,耳朵微張著,似乎你的腳步聲打斷了它的午餐。
走了一百來米,過一條小木橋,路忽然左拐,眼前真正地“一片豁然開朗”。一個異常美麗的寬闊的山谷、一座黃墻泥瓦的農家小院、一大片開著繁花的桃林、炊煙和黃狗的叫聲呈現在你眼前。我的肥胖的、慈祥的、穿著灰布衣服的外婆聽到狗叫聲,從灶房里走出來,手搭涼蓬在門前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