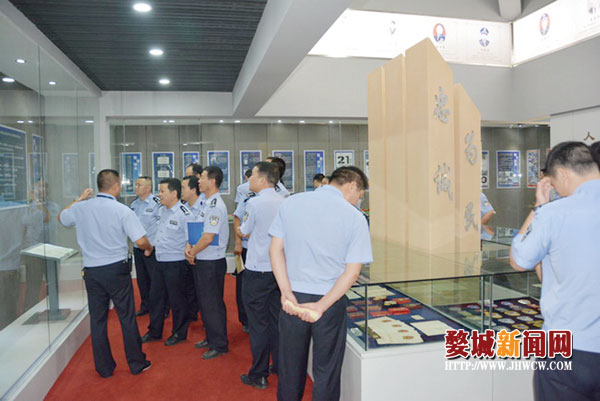一個五十歲的男人還沒有結婚,能不能稱為老單身漢?對于這個觀點他有些飄忽不定,仿佛他一直都生活在年輕的時候;只有當別人不怨其煩地議論他的身事,剛好又被他撞上,那時他才會悲哀地感覺似乎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再也沒有年輕的時候了,一個去年剛成為寡婦的女人好幾次這樣說他。以至于他一看到她們挨著門墻低聲地說話,就會不由自主地虛構那些重復的內容,此時他必須從她們身旁經過,她們停下來以女人的目光看著他;從前,他會點點頭示意,也不知從哪次起,他變得像個夢游人一樣忽略這些婦女,悄然地踏上通往樓上的階梯。然而他的心是不平靜的,有一次樓下的女人半認真地要把寡婦介紹給他,他委婉地拒絕了,過了許多天,兩個女人似乎都忘記這件事情,現在他向她們顯現這種表情,是不是會把事情弄得毫無挽回的余地呢?其實那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但事情過了這么多天,那種邂逅式的征求他意見的眼神再也沒有出現過,又讓他感覺這個寡婦其實也不錯。他需要女人,他不想單身終老,好幾次他匆匆從樓上下來,剛好迎面遇上她,心居然會砰砰直跳。他暗暗觀察過她的胸部和裸露的肌膚,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給人的錯覺對他這種沒有經驗的男人來說是致命的,有時他在她后面上樓,她最美的形象通過扭動的臀部以及結實的大腿傳達出讓他興奮的欲念,他真恨不得立即撲上去占有她。但是她回過頭來,看到他偽裝的淡然神情,也陌生地別過臉去,他又感覺到卑微,幸福已經一去不返了。
當他走進房間,狹小但散滿雜物的臥室里,看上去居然好像只有一張床鋪和一個衣櫥,站在衣櫥的鏡前留影,或者靠著窗臺隨意地觀望外面,他都能夠預感眼下這個居所將會變得更加孤單,真老了的時候,只剩下這個房間了,而這座房子比他年紀小很多,如果它有一天也老了,肯定是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那時他在哪兒呢?天知道。可是活著是需要一個伴的。年輕時他想養幾條狗,不過那多半出于物資上的復仇,因為沒有女人希望嫁給他,但養狗對他的錢包來說是綽綽有余的,他甚至可以省吃儉用,給它們買優質的口糧。現在這個念頭愈發地強烈,哪怕只養一只,隨便什么寵物都行,一旦它們愚昧但又溫馴地撒動四肢向他乞食,那么作為公寓中的一員、單位里的小職工,他殘留的支配心理多少能獲得平衡。為此他每天逛寵物市場,穿著他最好的衣服首先出入在本區最高檔的兩家寵物店;他極力表現出優雅的舉止,像個有錢的行家在為自己的小情人選購那樣,對寵物只要求美觀與健康,錢從來都不是問題;他收集了各方各面的資料,然后攢著這些知識圍著籠子細細地比較,漂亮的女售貨員們頭一次幾乎都會被他迷惑得屢屢溫柔地向他獻殷勤,讓他好不得意,他喜歡聞她們身上的香水味,冷不丁地但又溫和地和她們談話,等到她們驚醒了,她們靈敏的嗅覺用不了多長的時間辨出了他,于是鄙夷地一瞥,不再對他感興趣,最后屬于他的便是靠近郊區的、凝滯著動物腐尸及糞便臭氣的家禽街。
他倒是喜歡那個片區,只要他一出現,人們都能夠認出他,他不再是純粹的顧客,而是曾經的年輕郵遞員,他們的老朋友,因為從十七歲起,他就在這里投遞了二十年的信件,到后來通往的信件少了,又招來了投遞報紙的臨時工,他便坐進辦公室享起清福了。人們這樣評價他——不幸,還好得到補償,歸根結底又留下了遺憾——他應該結婚的。現在他走在這條街上,像回憶從前的生活,圍繞在關著貓和狗的籠子邊,他像對待戀人一樣隨意挑選,只要他看上哪只,店主一定會免費送給他。可是他是沒有辦法接受那么擁擠的空間里再塞進一個籠子,這算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他覺得這些土貓和土狗都沒有一絲高貴的靈性。他從這里走過,從年輕時開始,不知在籠子外觀看過多少次了,人們從他認真的神情里看到他的真誠,沒有人了解為什么他總是空手而回,還帶著失望,他像他的家一樣,充滿迷霧,而這樣又正好使得人更加同情和尊敬他。產生這種情緒是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感覺他缺乏什么呢?人們送給他自產的瓜果和蔬菜,雖然不值錢,但是他們的土地原本就變得非常稀少,他也接受他們的饋贈,總是在某一天的暮色中幽暗地提著,像是個受到誘惑侵害的病人,以至于他無法安置那些最終將脫水的食物——然而,記憶又不堪清晰地告誡他,毫無理由地將這里擴大一萬倍,那里拋棄得無影無蹤,倘若真相在它需要澄清的第一時間面對他,或者正值一個完全脆弱的人瀕臨最理智的那一瞬間,他收錄得到那些證據,他害怕它們,了解它們,那些營養學的分析、化學式的猜測、甚至是盲目吞咽地在餐桌上處理掉的所有殘余,從中得到的滿足就是催促他在告別他們時心存懷恨、妒忌和感激。他黯然地走過巷道,他在房間回想他黯然地走過巷道,好像坐享劫后驚魂的余生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