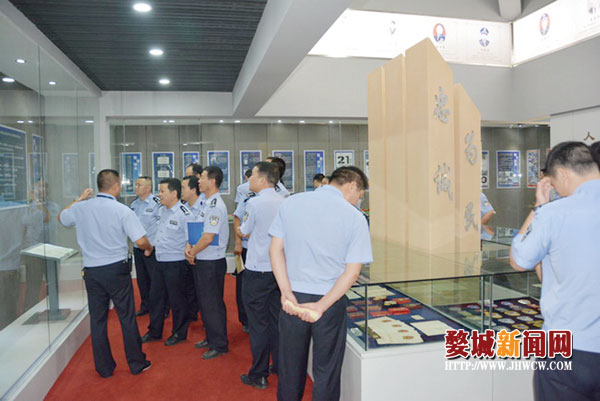近一年來,我再也沒有去過野外。過敏癥困擾著我,手上、腿上長滿了水泡與疙瘩,癢得厲害,最后連法國梧桐的葉子颯颯吹動,我都要心里發憷。我在想,完蛋了。我只能老老實實地呆在家里。
夏末,身上稍許好些。我偶爾也出門轉轉。鎮子里的巷子還有些意味。我往往繞遠,繞過靖海樓去畫廊。檐影交割,晦明相接,風時急時緩,在那里游蕩。高頎的水杉隔著院墻,不時把枯干的杉枝掉落在青石板上。這是巷子里的晴日景象。換了陰雨天,兩堵高墻濕漉漉地發黑,滑溜溜的巷道像面打磨出來的鏡子,光影可鑒。走到巷子盡頭,路沉落下去,接到了河邊,繼而被葦叢捉住,押送到一座小橋,再到橋對岸,一株高大的紫桐前來迎接。路已經變寬了,三岔路口,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直著向前,依次童裝鋪、香水店、琴行,然后,畫廊就在眼前了。
推開風鈴垂掛的玻璃門,畫廊主人見來了人,即去泡茶。我總是站在逼仄的過道前,先看一下兩只鳥兒。去得次數多了,八哥早就不像以前那般興奮,它在籠子里偏過頭來看我,脖子略伸一伸,縮回去了事。喜鵲則是俯低身子,好像隨時要沖過來,猛地給我一口。
我并不喜歡這只八哥,畫廊主人也不喜歡。它會在喉嚨里“哦嗬嗬”、“哇呼呼”地大笑,也會問好,餓了會說“吃~面”,渴了會說“喔(喝)~水”,當然也會說“再見”、“拜拜”。不喜歡的人它是不說的。見它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我于是拿根麻稈來逗它,隔著籠柵,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它也把頭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擺個不停。它氣得渾身發顫,翅羽也全部漲開,終于等到麻稈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啄上一口。我心想,有憤怒就好,總比我現在活得連憤怒都幾乎快沒了的好。游戲到此結束。
換了書店里的老太太過來,那是另外一副德性。老遠聽到那腳步聲過來,它就開始“嗯嗚嗯嗚”地哼唱,等到老太太推開門進來,馬上問好,拿了頭和身子在她手上挨挨擦擦,十分地親熱。鳥與人有緣,但要看和誰結緣。她既不養她,也不喂她,它卻偏偏和她要好,好得不得了,讓人見了眼紅。她就問它,“哦,他們欺負你呀。”它就“嗯~哇,嗯~哇”地訴說個不停。至于畫廊主人,除了渴了、餓了,它發出命令來指使,把畫廊主人當仆從使喚一樣,它再也沒有多余的話。
隔壁的琴行里有另外一只八哥。當年還是雛兒,臺風來臨時從苦楝樹上掉下來。畫廊主人因為早有了一只,也就把它送與琴行主人。它與琴行主人無緣,每天坐等的就是畫廊主人過去。忽然有一日,它飛出了籠子,棲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樹頂上,再也不肯飛回。于是,琴行主人趕緊打來電話,把下了鄉的畫廊主人急急叫來。畫廊主人把手攤開,“噓———”地一聲口哨,那鳥兒也就歡欣鼓舞地飛來,停落手上,豎起身,輪起翅膀,對著它“嘰哇”個不停。說時遲,那時急,手一攏,畫廊主人早把它握住,塞入籠中了事。自此,這鳥兒再也不理會畫廊主人,任它千百般殷勤,終是偏過頭不去覷他一眼。緣分已盡。
畫廊主人的這只八哥,現在整天內心郁結,心事重重。除了癡癡地等那個她,它別無它想。主人有時心里薅惱,忍不住會去碰一碰它,它也不吭不啄。終是你養著我吧,也許它是如此想的,任你來吧。但等到他的手一離開籠子,它馬上洗澡,用了喙引了水流,把全身上下洗個遍。主人有氣,再伸進手去撫摸,它也就再洗。兩方像賭了氣,如此反復,鳥兒洗過三四回澡,主人終是心里惻然,悻悻然離開。
喜鵲是畫廊主人的至愛。自從它掉下巢,主人把它從柴堆里撿起,一點點喂大,它就對主人忠心不貳。沒有人敢接近它,它那張嘴啄到手上,完全可以洞穿手掌。野外的喜鵲,它們不乏鍛煉,身子精瘦,幾乎沒有一絲贅肉,我從鳥網與獸夾上解下它們,從頭至尾,摸上去就是一把“駁殼槍”。這鳥兒在籠子里長大,雖然個性十分活潑,總是不停地跳躍,啄木頭,但身子還是要圓胖一些。它也愛干凈,總是及時打理自己的羽毛,十分光潔。但比起野外的鳥兒,終是要差一些。鳥羽上的那種鋼灰色,是因為長期飛行,血液通過毛細血管一直盡力送到羽端,煥發出來的顏色。這些螟蛉子的羽毛終是要遜色許多。雖然它的喙一天到晚總是不停地啄磨,如此地尖銳有力,但隔不了多長時日,主人也不得不用剪刀幫它修剪一番。
這鳥兒自知命運,倒把畫廊主人當作自己的親人。主人待它如此之好,它也會幫著主人收拾桌上的小東西,諸如掛件、筆筒、打火機、耳勺,無論主人如何亂丟,它總會叼來,置于一處,暗暗地收藏。籠子門不用鐵絲擰上,它也會自己拱開籠門出來,自己進去,玩夠了關上籠門。倘若主人要吃牛肉干,它也會幫他剝開,看著他吃下,偶爾也討主人歡心,嘗試著吃上一口兩口,待到主人吃完,它就把一張糖紙寶貝似地收藏。它也明知主人不喜歡那只八哥,兩只鳥兒若是一齊放出,瞬間它就能騎在八哥身上,作勢要啄,只待畫廊主人一聲令下。主人又哪有那樣的心思呢,是它揣摸罷了。看到主人著急的樣子,它也就放開八哥,飛到高處炫耀自己的力量。喜鵲的智商竟是如此之高。
海寧有一農戶,梨地里的大桑樹上有一個鵲巢,人與鳥一直相安無事。一日,農戶同幫工在樹底下用中餐,聒噪不停。鵲巢中的鳥兒竟然飛出來,在他們頭頂上拉下一泡屎。農戶窩心不過,用竹竿直接捅翻鳥窩了事。喜鵲是遷居別地了,但事情遠遠未完。待到梨兒半熟,這只鳥竟然引來一大群喜鵲,在每只梨兒上啄破,不多不少,只啄一洞……我曾在野外看到喜鵲選取配偶的聚會,也曾見到喜鵲送葬的場面,此前有文詳述,于茲從略。我是說,喜鵲的智商,相較于人,也毫不亞于。
南門某集貿市場,肉鋪主人也養有一只喜鵲。我每見這鳥兒在菜市里廝混,同各個攤主都混得格外熟絡,它也會覷乖討巧,討要吃食。也許它還知道這菜場里的勾當,竟然會趁別的鋪主不注意,偷偷叼了硬幣回家。喜鵲對閃閃發光的東西感興趣,多有在妝臺上丟了戒指、鈴鐺、手串與項鏈的,恐怕與之也不無干系。如前所述,喜鵲多有人的習性與心智而已。
無論如何,螟蛉子心里恐怕都有自己的隱衷。把它們放出去,也不會和野外的同類混作一群。喜鵲是這樣,八哥亦然。它們和自己的同類隔著距離對望,既不呼喚,也不做出某種肢體語言,只是相互凝視一陣,然后各自飛走。這是十分有趣的現象,留待我以后深究。我心下里以為,鳥兒之間應該會感應到對方的體型與力量,對方的生活經歷。有沒有沾染人的氣味,或者說塵世的氣味,那可能是最直接也最易感受到的。這些螟蛉子,幼年失怙,如此的生活,怕也是迫不得已了。
云南人某,我見他在花鳥市場一聲唿哨,籠子里的畫眉便躁動不停,馬上朝向他婉轉鳴叫,恨不得立刻沖開籠柵,跟著他走。他也十分了得,一般的畫眉根本不入法眼,他只是稍作逗弄,便即刻走開。他自述家中有一只畫眉,但也不是“頂尖兒”的,雖然那只畫眉生活月用都已高過他的用度,他還是有些失落。他去南北湖的山里捉畫眉,空手而去,不帶任何鳥具,他吹一種奇奇怪怪、低沉又荒落的口哨,就有畫眉飛來他的手上。心甘如此地跟隨他,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許,他吹的是那雌鳥兒的小曲?好在他只為尋找他心里的那只畫眉,從不愿為惡,他端詳一下,聽一聽它的鳴叫,也就嘆著氣放了手上的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