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他堅(jiān)信“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里都會有”
李建宏是一個(gè)90后,從云南昭通到寧波,他未嘗想過道路既阻且長;從寧波橫漂東陽,他也未嘗想過路漫漫其修遠(yuǎn)。他說自己是靠感覺生活,這是值得驚異的,是否真有全靠感覺生活的人,我們不知道。但他言之鑿鑿,正是因?yàn)榍嗄甑闹練馑凇K阪某桥臄z美德好少年倪諾時(shí),感觸可謂深矣,每個(gè)人立身之正,在乎教之使然。盡管天性上有仁德,后天自然更要“養(yǎng)仁培德”,方不失做人的本義。李建宏說,他所生長的地方并不見得好,但能夠自淤泥中振拔,全然在他母親的誨人不倦,立身為范。以致他后來的求索,更是堅(jiān)韌,盡管不似“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然他總在前進(jìn),魯迅先生說過,“自卑固然不好,自負(fù)也不好,容易停滯。我想,頂好是不要自餒,總是干;但也不可自滿,仍舊總是用功”,這在李建宏身上,也是可以見出用功的心氣,這是要對自己負(fù)責(zé),也是形成自己的生活態(tài)度。
母愛使他沒有傷害地長大
昭通是一座小城,其實(shí)昭通并不小,除去大理、昆明,它也是云南文化的發(fā)源地之一。昔時(shí)通往四川、貴州的門戶,除去昭通,別處真可謂是險(xiǎn)途。人說昭通是“鎖鑰南滇,咽喉西蜀”,今人早已不知其要旨。李建宏生在1991年的昭通,工業(yè)文明的氣息也早已遍布其間,遙想古時(shí)昭通作朱提時(shí),“產(chǎn)銀多而美”,不想終有一日朱提也成了主義。李建宏離開昭通時(shí),未嘗知道自己今后彷徨四五年的也是一座小城,不過這里離昭通已經(jīng)不止十萬八千里。他說:“我只是跟著感覺走。”那時(shí)他還沒有聽過蘇芮的歌,“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里都會有”,但他已然相信,夢想的事真的哪里都會有。
李建宏對自己讀書的事兒,極為簡練地概括為“小學(xué)在昆明,初中在昭通,大學(xué)在寧波”,其實(shí),他在昭通先是讀了一年小學(xué),隨后,因他的父親在昆明做生意,只好遷往跟讀,“不出幾年,我父親做生意虧了,家里也就多了個(gè)窟窿,我和妹妹跟了我母親,待到讀初中時(shí),因?yàn)槔ッ鞯慕枳x費(fèi)太貴,我們就回了昭通。”李建宏說。他對昆明的印象極其美好,四季如春,連空氣都是甜的。一回到昭通,他頓覺自己又陷身泥沼,放學(xué)路上,幾乎每天都可以看見打架斗毆,打群架更是習(xí)以為常。這也是他認(rèn)為昭通之所以“小”的由來。“我也不是沒打過架,可我媽每次都會懲罰我。”李建宏說,“其實(shí),和其他孩子一樣,我也喜歡打游戲,甚至偷錢去游戲廳玩,一打就好幾個(gè)小時(shí),回來鐵定要挨揍,揍完之后又是一頓教育。”盧梭在《愛彌兒》中說過,“我們不能為懲罰孩子而懲罰孩子,應(yīng)當(dāng)使他們覺得這些懲罰正是他們不良行為的自然后果”,在李建宏的母親看來,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近乎一個(gè)母親的教育天性。每個(gè)母親所能冀望于自己孩子的也就是“不能總是牽著他的手走,還是要讓他獨(dú)立行走,使他對自己負(fù)責(zé),形成自己的生活態(tài)度”,蘇霍姆林斯基的經(jīng)驗(yàn)更是一個(gè)長者的經(jīng)驗(yàn)。李建宏則說:“母親的愛使我在沒有傷害的環(huán)境中長大。”
因?yàn)椋母赣H能夠寄給他們的贍養(yǎng)費(fèi)并沒有多少,在昭通的威信八中,他除了埋頭苦讀,幾乎別無出路。直到四五年以后,他才想通了一點(diǎn),“當(dāng)初我爺爺在家鄉(xiāng)還是很出名的,他是布料廠廠長,誰想后來經(jīng)營不善,國家再也沒有撥款,他反而把自己的錢都投進(jìn)去,最后落得連個(gè)聲響都沒有。”李建宏說,“我父親恐怕也是心有不甘,做生意也落得一敗涂地。”在他鮮少的記憶里,他曉得自己的爺爺,不論國畫、蠟染、釀酒,都是個(gè)能手。除開這些,這座小城留給他的記憶寥若晨星,更不足為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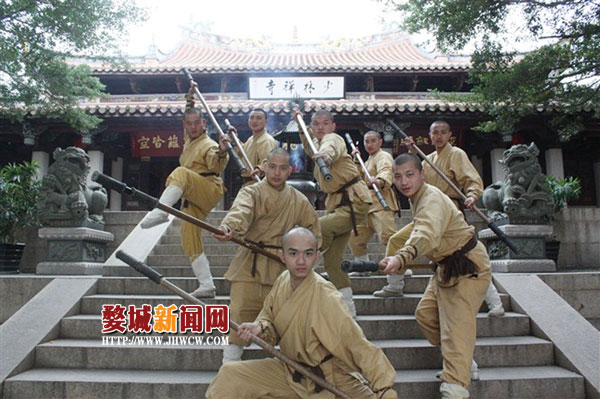 |
 |
堅(jiān)持既為了夢想,也為了證明
李建宏能夠逃離昭通,似乎更在于逃離一種失敗的惡感。連高中都未嘗讀過,他卻考上了寧波廣播電視大學(xué),讀計(jì)算機(jī)系不到兩年,轉(zhuǎn)而棄學(xué),欲北上做演員,卻鬼使神差,看到橫店亦有做演員的機(jī)會,不想就轉(zhuǎn)道去了東陽,時(shí)在2009年,趕上《新還珠格格》的檔期,但他第一次出演的卻是另外一部戰(zhàn)爭戲,在《圣天門口》里面串演一具“躺尸”,一躺就是一上午。當(dāng)他在《新還珠格格》里面演一個(gè)老百姓時(shí),僅有的一句臺詞“那個(gè)就是民間的格格”,到了最后,依舊作廢。
“原先,橫店在我腦海里是一個(gè)和古代城墻一樣滄桑的地方,可后來才發(fā)現(xiàn),它和其他地方并沒有什么差別。”李建宏說。那年夏天,他入了橫店的演員公會,凌晨三點(diǎn)出來討差事的日子更是常見。第一次吃上劇組餐,竟是一個(gè)獅子頭、兩片青菜,“這足夠讓我記上一輩子了。”他說。第二天他又串到《11公里》的劇組當(dāng)了一把群眾演員,隨后,又回到《圣天門口》劇組繼續(xù)當(dāng)跟組群眾演員,只因腿腳勤快,武術(shù)指導(dǎo)的助理相中了他,讓他當(dāng)了演員劉立偉的助理,后來終歸跟人“互不咬弦”,劇組開到上海他又立馬開溜了。通過朋友,李建宏又做上場務(wù),這回更讓他長了記性,“做場務(wù),一個(gè)配重30公斤,你身上要背四個(gè)配重,從公路一直往田里跑,后來身體實(shí)在吃不消,也只能放棄了。”他說。某年冬天,他和其他群眾演員只能穿劇組的臟衣服、濕鞋子……這一路走來,從演員到助理再到場務(wù),他既嘗到了甜頭,也吃夠了苦頭。
但他為什么沒有放棄?或許這是兒時(shí)的夢想,不能就這樣放棄掉。“我妹妹既漂亮又會跳舞,我父親就很喜歡她,經(jīng)常放歌給她聽,帶她學(xué)這學(xué)那,我只能默默地跟在后面。”李建宏說,“某種程度上,我想我要比妹妹更出色才行。這可能既是夢想,也是一種證明。”在橫店漂泊三年,并沒有動搖他的志向,甚至比以往更堅(jiān)定了他要走的路途。他結(jié)交了一圈友人,先是做場務(wù)認(rèn)識的路航,路航又介紹他認(rèn)識攝影師王哲,他跟王哲去杭州取景拍攝中央臺的紀(jì)錄片,殺青時(shí)王哲跟他說:“跟著我干吧,不要回橫店浪費(fèi)了。”可他最終還是回了橫店,轉(zhuǎn)而去拍古裝照,一邊專研做導(dǎo)演的學(xué)問。“在橫店當(dāng)攝影助理,只是為了生存。”李建宏說。
沒過幾年,橫店的DV游開始火起來,他就轉(zhuǎn)行當(dāng)導(dǎo)演,組建自己的團(tuán)隊(duì),開辦工作室,空余則在橫店影視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編導(dǎo)。他交游漸廣,眼界也隨之開闊,他的編導(dǎo)老師周詩雨帶他上京,上的是導(dǎo)演楊建國的課,在北京電影學(xué)院進(jìn)修一個(gè)月。等他回到橫店時(shí),DV游已經(jīng)讓他有點(diǎn)接受不了,“我真心想要開始拍電影了,而不是什么DV游。”他說。但他的團(tuán)隊(duì)還不成熟,于是,他也下了決心,“所有人都作鳥獸散”,去其他劇組或者影視公司各自磨練,“等到哪天時(shí)機(jī)成熟了,一聲號令,我們又會聚在一起,真正地開拍電影。”李建宏說。他從橫店轉(zhuǎn)戰(zhàn)金華,進(jìn)入微視傳媒當(dāng)策劃兼攝像,并且趕上拍攝《善美金華之倪諾篇》,并不是一個(gè)偶然,“機(jī)遇只青睞那些有準(zhǔn)備的人”。
除去做一個(gè)電影人的夢想,過兩三年,他打算去山里支教,做一個(gè)山里孩子們的老師,在山里安心寫劇本,以后就“師出有名”了。盡管昭通在他的印象中日漸淡去,而金華則是愈加地鮮明,可在二者之間始終維系著的則是夢想,“夢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為現(xiàn)實(shí)。”丁尼生說,“我們不就是生活在夢想中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