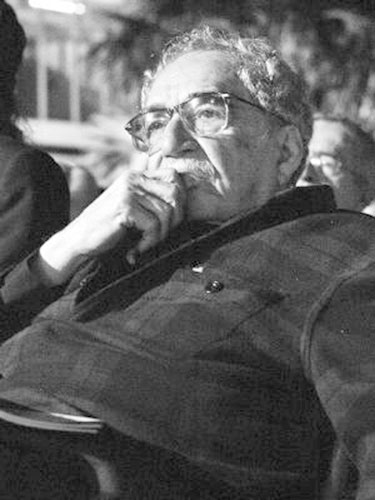
加西亞·馬爾克斯開篇寫到:“霍塞·阿卡奧迪·布恩地亞是村子里前所未有的最有事業心的人。他安排了全村房屋的布局,使每座房子都能通向河邊,取水同樣方便。街道設計得非常巧妙,天熱的時候,沒有一家人比別人曬到更多的太陽。短短的幾年里,在馬貢多的三百個居民當時所認識的許多村莊中,馬貢多成了最有秩序、最勤勞的一個。那是個幸福的村莊,這里沒有一個人超過三十歲,也從未死過一個人。”
2000年暑假,我隨同大學班級一起去麗水的一個小鎮實習,我帶不了多少書,帶的書中就有這本《百年孤獨》,因為幾乎沒有別的書可以讀,就反復讀它讀了七八遍。“這里沒有一個人超過三十歲,也從未死過一個人。”這一句話在我的腦海里一直存留著很鮮明的印象,我好像描述過兩次那些我讀它的早晨,坐在走廊的水泥護欄上,早晨的陽光晃動著穿過法國梧桐茂密的葉從,音樂專業的學生在走廊邊的教室里修《視唱練耳》,很明亮的女聲伴隨著太陽一點點升起的溫暖在身體四周回蕩,馬爾克斯筆下的形象也一點點地在內心深處扎下根來。我很懷念可以在夏天的早上伴隨著還沒有那么熱烈的陽光看書的時光,我自然也很懷念可以近距離聽到這么多明亮的女生發出同一個音高的聲響。
(這種懷念不管從描述角度或者從記憶角度來講都非常啰嗦,也當然是寫實性繪畫作品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之一。順帶說一點我對“啰嗦”這個事情的看法。啰嗦和讓人著急有一定的聯系,因為聽啰嗦的人說話,有時候的確是著急的,但它們同時也是兩回事,說話特別“簡潔”的人也容易讓人著急,會不會著急,其實是看講述者和聆聽者之間的關系。對大多數人來講說得見好就收的小說家也不多見,在能講清楚的條件下,我們只能越說越少,越說越短來保證我們不那么啰嗦。這是中國古人某些文體的傾向之一,是詩歌的傾向之一,也是所有實用文字的傾向之一,但是很可惜不是小說或者繪畫的傾向,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見得嚴格要求繪畫作品和小說作品一定要保持簡約的品性。但是,能夠讓人著急其實也是一種能力,所以技巧上來講,故意啰嗦〈連同結巴在內〉和故意隱藏掉某些關鍵點的“簡潔”能夠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張力。不過當我們的描述成本因為工業進步而大大降低之后,啰嗦得以大行其道是時代的缺陷,沒有多少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氣息,這些橫沖直撞的氣息到處在影響視聽,污染品性。什么東西能帶我們回到更純正的氣息控制的道路上,但是——這種控制卻只屬于個人判斷,卻不從屬于某種“完美”的體制?)
晚上重新翻開讀兩段,這一段給我的印象比起前幾年來有很多不同。在想象中,這樣的村子布局是否能合理地存在?我們需要知道哪些條件,計算哪些數據才能夠比較準確的在平面圖上勾畫出村子的布局?我們需要計算的是太陽高度是否會因為季節變化而改變日照時間,建筑之間的距離和太陽高度角有著很明顯的聯系。我們要考慮河流走向,要考慮集會場地,馬路的寬窄要視人流多寡而定,窗戶的高低要視照明需要而定,這里面幾乎涵蓋了所有人體工程學涉及的計算方式,當我們開始進一步的設想布恩地亞帶花園的餐廳的時候就更容易了解輕松的文學描述會給具體實現帶來多么大的難度。馬爾克斯并沒有刻意計算過這些,他也沒有計算的必要,這些必要隨著我想用畫面來表現的欲望的增強而越發變得有難度。不過這類想法充其量是個蠢笨的出發點罷了,但是通過這種純理性的方式或許可以體驗出越是涉及具體細節的描述中是否越能夠放入假設和虛構,本身沒有瑕疵的細節會因為細節和細節之間的關系而變得充滿矛盾或者充滿更多的可能性。
在許多肖像畫的成例之中,眼睛的神色和嘴巴是分離的,不容易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表情,卻可以表現出動人的一面。換句話說,我們講述往事時如果能恰當的塞入一些捏造的細節,反而能夠使往事本身顯得更順滑而真實,絕大多數的平淡帶上一丁點奇特的征兆,就是我們愿意相信的東西。“趣聞的囚徒”。不過,太有趣的事件頻繁發生,又顯然是讓人懷疑的。
畫面上的處理技巧也有相通的地方,怎么把大局處理的平淡不留痕跡,是靠近平穩氣息的方式之一,我不想說某種表現手法更貼近生活,這樣的表述和相關定義不能夠作為衡量藝術努力的標準,而只是狹小范圍內的可能之一罷了,并且并不帶著美的成分。氣息要轉動,看的是轉動的人的能耐,梵高顯然是轉動的,純粹靠情感支撐創作,并且也把情感力量放在重要位置的所有門類的藝術家的通性在于將狂喜或者不幸認定為生命經歷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除了命運本身的節點能夠導致的可能外——垂問命運其實是在向上帝撒嬌?——自然還有更獨立的人的行為可能性。不管是可喜的還是可惡的,都有可能是我們的“人性”中的一部份。
假設任何結論并且尋找例子來證明,這樣的尋找本身就具有虛構的成分,虛構一個人物,虛構一種氛圍,虛構一個理論,虛構某種需要,這些虛構在填補的東西,有人曾認為是神創造的世界的縫隙——因而我們的世界不可能是真實的。如果我們停止關注這些虛構,并且也一樣停止試圖用更巧妙地虛構來填補我們自身存在的虛無感,我能夠體驗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回環。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經不住三次回環的,又長,又有鋪墊,具備巧妙結構的趣聞會因為自身的巧妙而變成死結,如果不主動開放格局和遺漏必要細節讓同一個故事從此變成另一個故事,談話的對策就會變成以回環對回環,用死結反死結。聰明的腦袋拒絕冗長的簡單算法,這也應該是從圖案對比的快感到形象鮮明的快感的轉變的起因。
尋找某一些“對”的結論的努力本身也許是錯的。喜歡下結論的人生往往到頭來會被自己噎死。有一些人相信藝術是關于如何真誠的努力,有一些人則相反,認為藝術是關于如何成功的實現欺騙意圖的努力,我們面對虛構卻恰恰好像在面對真實,同樣的虛構材料可以實現不同的意圖,對我來說,氣息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活著,欺騙是真實的,虛構是真實的,死結是真實的,啰嗦是真實的,因為這些不需要被證明,也絕不容易被推翻。那么,藝術作品中除了這一些糟糕的東西之外剩下的好質量,卻恰恰有可能并沒有真實存在著,認定和否認命運的都因此而顯得更為可疑,于是,所有的情緒也變得可疑起來了吧。
關于一個美人的所有的想象都有可能是真實的,但是快感卻恰恰在于虛構,異性之間張力的存在價值,恰恰要基于實現之前的所有無用的鋪墊,這些鋪墊越是一文不值,越是激起其中真實的成分,也越是能夠準確地黏住虛構和虛構之間的縫隙。越是消解掉現實層面上在畫面中出現的可能性,就越是能夠靠近繪畫活動本身的真實,我們從來都不是用真實來抓住對方的心,我們所能夠動用的資源,唯有虛構而已。
到現在為止,文學所能夠給我的最深層的力量,最好是看得完整,然后丟棄,再過多少年也不必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