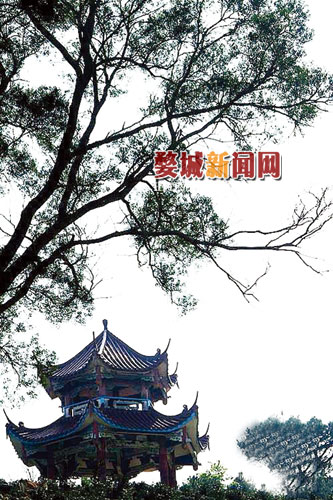
數(shù)不清的疼,生生往它的懷里揣/那朵草兒,那朵柔弱的光/硬是扎下了根來(lái),為倔強(qiáng)隨風(fēng)起舞/亂發(fā)拂面。草兒不顧一切/拂進(jìn)它的深處,/那里幽暗、柔軟,別有洞天/驚慌是它溫柔的秘密
——《石頭》
為了在這塊干凈的石上生存,那簇柔弱的草一定是費(fèi)勁了心思。一如我此刻的潛行與窺視,誰(shuí)能看清我眼前的神話——除了時(shí)光。它們不說(shuō),它們徑自糾纏到了一起,牢牢地抓住彼此,拽住此刻我的視線,而我,正抓住了你。你總該滿足了吧?你雙臂交叉在胸口,帶著不屑的語(yǔ)氣問(wèn)我。那不是你我所能承受的經(jīng)歷。可你相信嗎,那塊石頭上刻著一個(gè)地姓氏,隱約的姓氏。它是我的外公。它也姓洪。你一聲不吭,拽著我走出了這座幽幽的深宅。
深宅坐落在壺公山腳,朝陽(yáng)一縷忽然的斜射,便將我們與它一同暴露在燎眼的金黃之中。而更遠(yuǎn)的一切,仍在陰影中甜美地打酣。叫醒它們不是我的責(zé)任。我們抬頭看看山頂,沿著山路繼續(xù)這未知的目標(biāo)和未知的路途。這山路,在走著走著以后就不成樣子,不成現(xiàn)在的模樣,你我也不成現(xiàn)在的人。
登上山頂,未知是怎樣一個(gè)不確切的詞,可上去了還有一個(gè)目標(biāo)就是得下來(lái)。我們要上去做什么呢?看日出,太陽(yáng)早出來(lái)了;鍛煉身體,這應(yīng)該是在于過(guò)程;鍛煉毅力,還有更多種的方式;吹吹風(fēng),看獨(dú)特的風(fēng)景?我想到這里便站住了。目標(biāo)或者目的這樣的詞語(yǔ)在我的腦海里越來(lái)越模糊,越來(lái)越可疑,當(dāng)我不得不說(shuō)出口的時(shí)候,你哈哈大笑:“是的,我們只不過(guò)去吹吹風(fēng),看看風(fēng)景!何必假崇高呢,活著,做事情就要簡(jiǎn)單一點(diǎn)才能享受樂(lè)趣。”
我的臉上一定是越來(lái)越充滿陽(yáng)光了,腳常常被路旁的小刺割到,還有些小蟲子叮我。我樂(lè)意被自然這樣親吻款待,真的。它們一簇簇生活在一起,很是幸福。走過(guò)這段路,前面一級(jí)級(jí)的石階越來(lái)越大,越來(lái)越難爬,后面我們只是踩著那些大石頭上去。不過(guò)坡較平,一點(diǎn)都不危險(xiǎn)。我瞥見(jiàn)一簇簇草孤零零地扎在這塊那塊石頭縫中,它們卻很是強(qiáng)壯。它們貴姓?它們是否費(fèi)勁心思?
我始終逃脫不掉時(shí)光的追捕。我無(wú)法在充滿回憶的帷幕中只看到陽(yáng)光和風(fēng)。這些可愛(ài)的景致,打開(kāi)它們的故事,將人兒畫進(jìn)我的瞳孔,看不見(jiàn),但我知道。那些是與我有著牽連的傳說(shuō)、物件和風(fēng)。它們?cè)诮?jīng)過(guò)時(shí)留下了痕跡——我頓然知曉了,這目的之外的沉醉。
那座深宅姓李,我也姓李,但我不認(rèn)識(shí)它。我只是想起一些事情來(lái),關(guān)于我的外婆。說(shuō)到壺公山,我就會(huì)想起水,想起水我便想起某個(gè)地方有座橋,它在某處,是否年代久遠(yuǎn),是否早已消失,都已不重要。而它與一個(gè)人的生命有關(guān),年代有關(guān)。外婆幾經(jīng)家庭迫害,曾經(jīng)站在那座橋上,翻過(guò)橋欄,躍入水中,只為成為自由的魚。外公的意外出現(xiàn)也像只魚,奮力撲救,召回了她。順帶的,才有了我媽媽,才有了我,以及還沒(méi)來(lái)得及出生的我的后代。這一瞬間是多么重要,如果所有人的瞬間都能被改寫,那么這部中國(guó)歷史也得重新編寫了。我看到的那石頭上的草,一定姓田。它扎根在那塊姓洪的石頭里,是多么富有寓意。這愛(ài)情我不說(shuō)詩(shī)意,生命如此沉重,詩(shī)意兩個(gè)字是遠(yuǎn)遠(yuǎn)承受不起的。
為了使那簇柔弱的草在石上生存,那塊堅(jiān)硬的石頭一定是費(fèi)勁了心思。我緩緩地對(duì)你訴說(shuō)著一點(diǎn)一滴并不吸引人的故事,你一路上沒(méi)有插話。你只是緊緊地拉住我的手,不斷提醒我要走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