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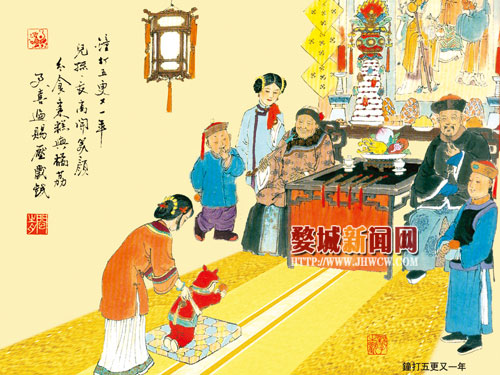


���������f(shu��)�������ː�(��i)���f���Լ�Ҳ�S��������ˣ���Щ�꣬�|�����飬��(j��ng)����(hu��)����������S�����£������nj�(du��)���r(sh��)��ijЩ��Ȥ��ӛ���q�£��v�v��Ŀ���vʷ�l(f��)չ�ˣ��r(sh��)����ͬ�ˣ�����l�������(hu��)�h(hu��n)�����O����^����(d��ng)����r(n��ng)���fò�Ѳ���(f��)�����ˣ����҃��r(sh��)��(j��ng)�v�^(gu��)���S���£��ڽ�������(hu��)��Ѳ���������һ�������ꃺͯ�������جF(xi��n)����ζ�҂����r(sh��)����һ������X(ju��)�úܶ������ʮ����Ȥ���ڴ��Ұ���ӛ���(l��i)��ʾ�ڴ�ң�ʹ��һ݅��ͬ־����ͬ�У����p��һ���������⣬�@Ҳ��һ���^�������x���¡�
�������u(����)
����ÿ�����£������S������(ji��)���������Ұ��ǝMMĽ��Sɫ�����У�����(hu��)��Ϣ���ܶ�ܶ�Ĵ��СС�����Sɫ�ġ��Gɫ�ġ���ɫ�����u���������﹡�ϣ�������һ��������Ҋ(ji��n)���傃һ��(g��)��(g��)����ͨ��ͨ�����������У������ڵ����
������������u�����H���҂��r(n��ng)�僺ͯ��һ�����£�Ҳ�Ǽ��L(zh��ng)��Ĭ�S�o���ӵ�һ�(xi��ng)���r(n��ng)������u���棬�����u�ֿɮ�(d��ng)��ʳ�ã��r(n��ng)�Θ�(l��)�����飿
�������u���k���ж�N��������ֱ�ӓ�ץ�ģ�Ҳ���þW(w��ng)���W(w��ng)�ģ�߀���������ģ����҂�����������ភU឵��k����
������һ����s2���L(zh��ng)����U���U�^˩һ���������L(zh��ng)�ļ��������ڼ����^���һֻС���u��Ȼ���҂�����U�����У������ַ��£�������������˷���(f��)������(d��ng)����������(hu��)�����T��Щ�����ڵ����g�����u����������(d��ng)���^(gu��)���˶�ã��͕�(hu��)��һ����(g��)���������Ă�(g��)���u�����^(gu��)��(l��i)����(zh��ng)�����Լ����^���������ǂ�(g��)С���ܣ��������ȵǣ��϶����ǂ�(g��)��(qi��ng)��(sh��)���Ȱl(f��)���ˣ�����ҧס�˾Ͳ��Ϸ��ɣ�Ȼ�����현�(sh��)һ�ְ���U�ጢ����(l��i)��������һֻ��Ѹ���쌢�^(gu��)ȥץס�ѽ�(j��ng)���^�����u����(d��ng)Ȼ��(d��ng)��Ҫ�죬��Ȼ��r��(hu��)׃�������uҲ�Ǻܾ��`�ģ��r(sh��)�g���L(zh��ng)�����X(ju��)����r����(du��)�����R�͕�(hu��)Ó�ڣ�������֮���Ǿ�ǰ���M���ˡ�Ȼ�����҂��@һ�ͺ��ӣ�Ҳ�����н�(j��ng)�(y��n)��������ֻҪ�їU�ӷ���ȥ�ˣ��������ֵ��܁�(l��i)�����T���^(gu��)һ����(g��)��^����Ҳ���(hu��)�ю�ȥ����t�b�ó����ķ��Żؼҡ�
����Ϧ�(y��ng)���£�����һ���r(n��ng)��Ĵ��˂����m(x��)�m(x��)���r(n��ng)�����չ���(l��i)�������࣬ϴϴ�֣���ץ�o������ˣ�æ�T��˶������ӣ���҇�����������㣬��?y��n)������IJ������ֶ���һ�P��ζ���ȡ����t�����u��
����ժ����
�����f(shu��)��ժ���ӣ���(sh��)�H��͵���ӣ���?y��n)��Ҽқ](m��i)�����ӿ�ժ��
�����҂��岻�h(yu��n)���Ђ�(g��)�ڸ��r(n��ng)��(ch��ng)���r(n��ng)��(ch��ng)���ڱ���ɽ�_�£���ɽ�ϷN�кܶ�ˮ���������ӡ��н��ӣ�����������ӣ����Ԉ�(ch��ng)���˹���ɽ�л���ɽ��
���������^���r(n��ng)��������࣬һ���һ���裬�����@�ֲ赭�֮�⣬ƽ����Մ�����Ђ�(g��)�ϰ������ćL��(g��)�r���҂��@Щ��(g��)�r(n��ng)��ĺ��ӣ�����(ch��ng)���˳���ġ��L��ģ�ֻ������ˮ���ɵ��ۡ���(d��ng)ȻҲ���BƤ�ĺ��ӣ�Ҳ��(hu��)�ڳÈ�(ch��ng)��ܹϹ����˲�ע�⣬����đ�ӣ��@�M(j��n)���ӣ����M(j��n)�r(n��ng)��(ch��ng)�Ĺ�ɽ�ϡ��ϵ��͵��һ�ѣ�����Ҿ�������һ��(g��)�ɡ�
����ӛ���������µ�һ�죬�҂�?n��i)���(g��)���p�Ļ�飬������������ô�ϻ���ɽ��һ�ѡ����죬�҂�����������������߀�����b����ɽ���_(d��)���_(d��)����(d��ng)Ȼ�ǿ����֣�Ҫ���ႀ(g��)�@�ӿ��ӵģ���(ch��ng)����߀�ܷ��҂���ɽ���ߣ�����һ��ӣ��D(zhu��n)�˂�(g��)�����҂��ͳ��˲��䣬���M(j��n)ï�ܵĹ���(sh��)����ȥ�ˡ������f(shu��)��������ﲻϴ�֣�ˮ����(sh��)�²�̧�^�����҂���Ȼ���ں�߅�ߣ����в���Ь�ĵ���������(g��)�˶��ڹ���(sh��)�£�ժ�˾ͳԣ��Զ��ˣ��L���ˣ�������ͣ��������ӣ����룬Ҫ�Ǿ��@�ӿ����ֻؼң��ĕ�(hu��)���ģ���ô�k����ԓ��һ�c(di��n)��ȥ�ɣ��֛](m��i)�@�����𰡡�ͻȻ����˂�(g��)�k�������˶�Ó���Լ����L(zh��ng)ѝ�ӣ���ѝ���Ç��řڵ��K�ӽ��˂�(g��)�Y(ji��)���ٰ��Ǵ�(g��)��(g��)�������b�M(j��n)ѝ�ܣ����ڼ��ϣ��ͳ����R�_(d��)�ӣ��҂���(d��ng)?sh��)��˷Q���R����Ȼ���҂�؈�������ĵ��ߵ�ɽ�_����߅���ò����ݵ��k�����������⡣�ؼҺ��҂������ӵ��ڻj���һ�B���˺Î��죬��ˬ�졣��ģ�һ�����ǂ�(g��)��ζ��(l��i)������߀�����X(ju��)������ġ�
��������
������Ԓ�f(shu��)�������ηN�С�����^(gu��)�ꡣ��Ϧ�^(gu��)�������꣬�������(l��i)Ҫ���꣬���ꌦ(du��)���ӂ���(l��i)�f(shu��)����һ����ʹ���������d�^���¡�
������?y��n)�������ɽ���ˣ������Ҽҵ��H�ݶ��Ҳ��ɽ���^��ÿ�������҂���Ҫ��ɽ���H���˼�ȥ���ꡣ�r(n��ng)��Ă��y(t��ng)��(x��)�T�ǡ���һ�ڼҲ����T��������������Ⱥ��������҂������������˵��˳�����һ�����͕�(hu��)�����춼��ø��磬�������·�����Ь�ӡ����m�ӣ����ϸ�ĸ���ѽo��Ҝ�(zh��n)��õİ���YƷ�����������c(di��n)�ģ��ɴ�玧�I(l��ng)��?f��)�������ɽ���^�M(j��n)܊�ˡ���ʮ�������ɽ�^(q��)δͨ܇��ȫ��һ�p�_���������H�ݡ�����·;�h(yu��n)�����҂������ȵ��˾˼ң��ٵ�����ң�Ȼ���DZ���ң�����̋��ң���һ����һվ����һ�ҳ�һ�ͣ��l(shu��)�ҳ���������l(shu��)��סһ�졣
����ɽ���˺ÿͣ���������õ��д�������һ���������ݟ���������c(di��n)�ģ�ÿ����ǰ߀Ҫ���σɂ�(g��)���u�����҂��@Щ������ƽ����յĸF�����ܴ˺��Ҳ���Ǻø����ˡ�Ȼ������ϲ�g�Ե�߀��(sh��)��Ŵ�����Ĝ��A���װġ�ܛܛ�ģ����������������������W�������(��i)�ԣ���ϧÿ��һ�룬���ܶ�ռ��
������^(gu��)�衢���^(gu��)�c(di��n)�ģ�Ȼ���������غȾƳ����С���ӂ��Ͳ�ס��ץ��(g��)�z�^�ÉK�⣬������������ݲݾͽY(ji��)���˿��磬���Ǻñȳ����f(shu��)���ǘӣ����ÉK����A�z�^����������ó��
��������ҵ��Tǰ�Зl�ӣ��ӵČ�(du��)������ɽ�����^(gu��)����҂���ϲ�g��ɽ��һꇣ�����ÿ�ζ���������Խ�^(gu��)��С����ˮ�������Ǽ�(j��)��(j��)ʯ�A��Ȼ�����D(zhu��n)�����cС��������������ɽ�֣�Ҋ(ji��n)��(sh��)��������С�B(ni��o)�� (t��ng)�����Ї\�\�x(ch��ng)�Q��һ����ݣ�һ����ľ������ƽԭ�˲���Ҋ(ji��n)���^(gu��)�ģ����Ǻ���O�ˣ�ż��߀��(hu��)�Ę�(sh��)���бij�һֻҰ�ã���(du��)������Ū�죬���������^(gu��)��(l��i)��ץס������˲�g�֕�(hu��)�������ǰ��ʧ�ßo(w��)Ӱ�o(w��)ۙ��
�����̋������h(yu��n)��סˮ��(k��)����߅�������Ҳ���Ҫ��ɽ��߀Ҫ��ˮ���s�ϔ[�ɵ�ľ������a߀Ҫ�Ђ�(g��)��С�r(sh��)���ܵ��_(d��)�˰���ÿ��������������ˮ�У���Ҫ�o���I(l��ng)��һ������Ȼ��̧�^���죬�·��Ǵ����У��������ڄ�(d��ng)��ɽ���ߣ����ۭh(hu��n)����ܣ�Ҋ(ji��n)����ɽ�Gˮ�B��һƬ���L(f��ng)���箋(hu��)�������գ�ӛ���������x��һ�����m�����R(sh��)�ֲ��࣬�sҲ�����Ў����p��Ȼ����Ȥ������ˮ�У����뮋(hu��)�У������п��f(w��n)ǧ�������ں��(l��i)�������У��Ҿ��Դ˞��}�Č�(xi��)��һƪ���ģ������ώ��o���Ҹ߷֣����ڌW(xu��)У�T�ڵĉ���(b��o)�Ͽ��dz���(l��i)�����L(zh��ng)ƪ�۠�����ӛ��ס�����Ў���������δ����ӛ�����@�������ģ���������ɽ���{(l��n)�죬������̎���˟����箋(hu��)�L(f��ng)��ӳ��ˮ�����X(ju��)С������ǰ����
�������T��������ζ�����Եúá���úã�����ʹ���ӂ����dȤ��߀�ǵȰ���Y(ji��)����ÿ�˶����ԏĸ��Ҹ����յ�һ��(g��)��t�������t�������У��d�²����У��x�_(k��i)�H�ݼң����ȳ���ڣ���Ҿ��Ȳ������ظ��Թ��_(k��i)�Լ������ܣ����_(k��i)�t����������һԪ������߀�Ƕ�Ԫ����������l(shu��)�ҽo�İ����l(shu��)�ҽo�İ�С�����l(shu��)�õ��X�࣬�l(shu��)�õ��X���١�����(l��i)���@�|������(l��i)�͐�(��i)�X��
��������ɽ���ɽ�⣬ɽ�����H�ݾ͛](m��i)��ɽ������ǘ���ζ���ˣ�һ�t�](m��i)ɽ?j��ng)]ˮ�](m��i)����ģ����t�^(gu��)����˸��X(ju��)�](m��i)�óԵģ�60������r(n��ng)���r(n��ng)������࣬��(j��ng)��(j��)�l����^(gu��)������ʮ�����ԭ�Ȝ�(zh��n)���һ�c(di��n)��؛Ҳ�ͳԵò���ˡ����^(gu��)ȝ�ijԶ��ˣ�����c(di��n)�صģ�ꐵijԅ��ˣ�ԓ���c(di��n)�r�ģ���Ԓ�f(shu��)�úã�������ݵ�ʮ���������r�������r�⡱���@ԒҲ�����Ǒ�(y��ng)���ˡ�
�����D(zhu��n)����ʮ�����^(gu��)ȥ�ˣ���С�������ˣ������굽���꣬�����H���f���������f�����^(gu��)����ô�óԵġ���õģ��s��Ҳ�Ҳ������r(sh��)���ǷN���X(ju��)�ˡ�
�������Ӱ
�������Ӱ���@�ǃ��r(sh��)һ�������d�^���¡�
������ʮ����������xС�W(xu��)���Ǖr(sh��) (t��ng)�f(shu��)����Ҫ���Ӱ�����ǿ��O�ˡ�ƽ�r(sh��)��ɷ������a(ch��n)�(du��)�L(zh��ng)Ҳ��(hu��)�����_(k��i)������T����������ǰС�낀(g��)�r(sh��)���ݹ���ÿ���@�N���ӣ���ĸ�ļ҄�(w��)�ֹ�Ҳ�dz����_������eĬ�������H������ĸ�H�������ˣ������������˾������ˡ��҂��ֵ܂z��Ҳ�����������ǘӣ��ŌW(xu��)�ؼ�߀Ҫ������@ȥ���i�ݡ�
�������^(gu��)������������Ů���ق��������(sh��)�����s��һ�ӣ������Ⱥ�ؽY(ji��)�鿴�Ӱȥ�����˂����ϔy�ף����ӂ�������С��Q���˕r(sh��)�d�İ���Ь����·����һ��L(f��ng)��������ó��ǻ��������^(gu��)�ģ����Bס���^�dz������D�](m��i)���D�Ĺ���h�������@�ӵĶ�һ�ӣ���(g��)��(g��)Ę���@���d�^��ϲ��Ę��ӡ�
������(l��i)���Ӱ��(ch��ng)�����˂����Ԃ�(g��)�������ӣ��҂�(g��)���m�ĵط����������pС�����tϲ�gվ(ռ)�v�Ɏ����r(sh��)���r(sh��)��߀Ҫ�������£���(j��ng)��Ū��Ӱ��(ch��ng)�𡰲��ˡ����҂��@Щ���ӣ��s�����Լ�����(x��)�T����һ�K��ʯ�ӣ����ɽ��ƴu�K���Rˢˢ��ϯ�ض����������^���������샺���۾�һգҲ��գ�ؿ��Ӱ��
�����Ǖr(sh��)���Ҹ������ĺ��ӂ���һ��(g��)��˼ϲ�g����(zh��n)������Ƭ��ÿ��(d��ng)�����yĻ�ϳ��F(xi��n)����һ���S�W�W�t�ǵ�Ƭ�^���͕�(hu��)�鲻�Խ��ع��ƚg���������̵ģ����̵ġ���������Ҳ�������Ǖr(sh��)���^(gu��)�ġ��F���Γ��(du��)������ƽԭ�Γ��(du��)�������ϸʎX����Ƭ�м���(zh��n)���R�^����(d��ng)Ȼ��Ҳ�����˺ö�������Ƭ�����K(li��n)����Ƭ�еđ�(zh��n)���鹝(ji��)��
�����r(n��ng)��(ch��ng)���Ӱ��Ҫ�ȿh��ӳ�(du��)��(l��i)������Ӱ�ęC(j��)��(hu��)�࣬����?y��n)��Ǖr(sh��)��ؐ�ٵľ��ʰɣ���(j��ng)��Ҫ�������Ďׂ�(g��)�r(n��ng)��(ch��ng)�g��Ƭ�ӣ���ˣ��Еr(sh��)���^(gu��)��һƬ������Ҫ�Ⱥö��r(sh��)���ܿ�����һƬ��ӛ����һ�����죬�҂�?n��i)��?ch��ng)����һ��(g��)��ӳ�K(li��n)����(zh��n)�Ĺ���Ƭ���ȵ���ҹʮ���c(di��n)�˲��_(k��i)�C(j��)��ӳ������ͬ��(l��i)���ˣ����Ȳ�ס�������ˣ���ʣ���҂��ׂ�(g��)�B�̷��ӈ�(ji��n)�ֵ��ף��ȿ���ص��ң�������c(di��n)�ˡ������҂��ֵ܂z����ĸ�ݺ�؟(z��)�R��һ�D��
�������r(sh��)���Ӱ���������d�^�ģ�Ҳ�������y���ġ�
�����~(y��)
��������С�������r(n��ng)��(ch��ng)���ҵ�����r(sh��)���������o(j��)��ʮ�������С�W(xu��)�����еĕr(sh��)��ÿ������٣��ҵ���Ҫ���(d��ng)�������i�ݓ����⣬��ϲ�g�����¾��ǵ��������ȥ�~(y��)��
�����Ǖr(sh��)����Ȼ��Ą�(d��ng)���YԴ�����S���������w�B(ni��o)�࣬ˮ�����~(y��)�ࡣ���쵽�ˣ������ˣ��~(y��)���ɾ����ˣ���߅�������^�������ˮ�^߅����ʹ�ڻĞ�Ұ���ﷲ����ˮ�Ŀӿ������У�����Ҋ(ji��n)���~(y��)��Ӱ����
�����r(n��ng)��С��ץ�~(y��)�Ĺ��ߺܺ�(ji��n)�Σ���(j��ng)����һֻ����������^һ�ţ����_ӭ�����ڡ�žžž���s���£�Ȼ���p�p����������һ�ᣬ��Ҋ(ji��n)��С�~(y��)С�r�������бı�����������ץ������ƨ�ɾ������~(y��)�r���M(j��n)ʢ��һ��ˮ��Ę����\(y��n)��õĕr(sh��)���Ҝ�(zh��n)�ط��¡��W(w��ng)�����Еr(sh��)һ�¾��ܓƂ�(g��)�����ɡ�Ҫ���㲻��̫�(y��ng)���������r(sh��)�ֳ�ȥ�������낀(g��)�r(sh��)�������㶼����һ����������Ľ��(l��i)��
����ӛ����һ�γ�ȥ�~(y��)����Ҋ(ji��n)һ�lС��ˮ�ܜ\���Ҕ�����Щ���ᣬ�{��(j��ng)�(y��n)���X(ju��)�ÿ϶����S���~(y��)�����@�����_(k��i)��(hu��)�����f(shu��)�r(sh��)�t���Ǖr(sh��)�죬�����������K��ˮ�σ��^�����½أ�Ȼ����Ę��һ��һ��ќ��е�ˮ�ܿ�Ҩ�M����Ȼ�������ϣ�Ҋ(ji��n)�ǜϵ��~(y��)��������һƬ�����L(zh��ng)�ޣ���܇��(�����~(y��)��)���а�Ƥ�~(y��)��������С�a�~(y��)��߀�������ﰵ�������q���S�X����һ�Ρ���������(zh��n)�����ۣ��ի@�Sʢ�����b�M�˴��Ę�裬���f(shu��)Ҳ�������
����߀��һ��������^��ˮ����(�f�r(sh��)����)�µ�ˮ���ж��~(y��)����һ��(hu��)�������X(ju��)���ε�ˮ���˶�ס�ˣ�һ�r(sh��)ˮ����p����ˮ׃�\����Щ�~(y��)�������ˣ��������n���C(j��)��ץ�~(y��)�ĺÙC(j��)��(hu��)���˕r(sh��)���� (t��ng)Ҋ(ji��n)ǰ��һ��(g��)ˮ����l(f��)�����W�W��푣����^(gu��)ȥһ�������ۣ������ˡ���һ�l���н�Ѷ��صĴ��T�~(y��)�ڜ\ˮ���΄�(d��ng)�أ����ǡ�̤���FЬ�o(w��)Ғ̎���Á�(l��i)ȫ���M(f��i)�������龰�mȻ���^(gu��)ȥ��ʮ��(l��i)���ˣ����������y������Ȼ�v�v��Ŀ���M�@��ǰ��
������(d��ng)Ȼ��Ҳ�е�ù�ĕr(sh��)���磬�Ў״���ȥ�~(y��)����ȥ�ĵط��������DŽe���˄���Ҳȥ�^(gu��)�ĵط���߀��(hu��)���~(y��)݆����ץ����Ǹ����˼�ƨ�ɺ��^��ƨ���](m��i)�к�̎��ֻ���ܚ⡣����һ�Σ���(d��ng)������ϵ�ˮ�����������Ǵ��~(y��)С�~(y��)�ۿ������ֵ��܁�(l��i)�r(sh��)���s�������Ђ�(g��)�e���r(n��ng)�����鿹����(zh��)��Ҫ�Q��̣�����ˮ��һ��(ch��ng)����ˮ���^(gu��)��(l��i)���o(w��)����ֻ�С������d�@����������һ��(ch��ng)�՚gϲ�������У��������M(f��i)�������в��ҵ��ǣ��Еr(sh��)��(d��ng)���~(y��)�����g�r(sh��)��ͻȻ��֪�ĺ�̎�Z��һ�l��ˮ�ߕr(sh��)������һ��������(d��ng)Ȼ�Ƕ���Щ��ò��Ȼ���䌍(sh��)���o(w��)��K��С�x(ch��ng)�T�ˣ������Dz���(hu��)�еģ�ֻ��һ��(ch��ng)̓�@��
���������������(g��)��٣�������Ҫ��ȥץ�~(y��)��������F(xi��n)�ڵ��r(n��ng)��С�����ڼ��#�棬�o(w��)�ε��Ǟ���ȫ�������r(n��ng)æ�r(sh��)���в�����Еr(sh��)���~(y��)���ˣ��ԅ��ˣ���ʣ�ˣ�ҲҪ��Щ��ģ��õ��ó�ȥ�u�ׂ�(g��)�X��һ���N�a(b��)���ã��Q�c(di��n)�ͣ��Q�c(di��n)�}��(l��i)�����ǿ��_(k��i)�W(xu��)�ˣ��e���c(di��n)��߀Ҫ���W(xu��)�M(f��i)��(sh��)�M(f��i)�ء�

���ij������P(gu��n)ע�ij����W(w��ng)��
<sup id="ecicy"></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