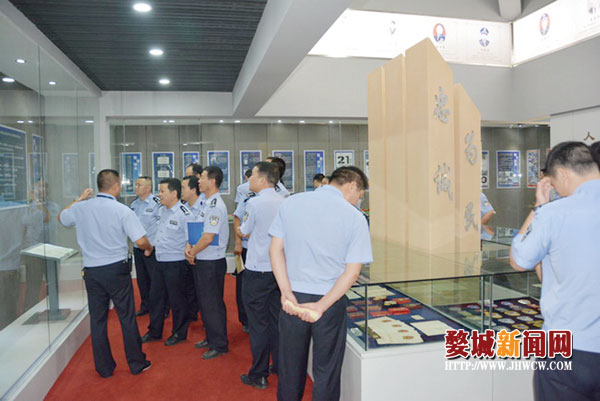蓬亂的衰草叢生在墻頭、街角、屋檐、門楣上、卵石縫中,在殘照和晚風中瑟瑟發抖。
從殘破的窗牖看進去,是傾塌的、霉黑的、橫七豎八的柱、梁、椽、檁和各種木質建筑構件,以及廢棄的生活用具:木床、木桶、柜子、桌子、凳子、蒸籠。清冷的、毫無人間生氣的灶臺上還留有“水星高照”四個墨字。遍地瓦礫。闊葉的、陰綠的植物在潮濕的廢墟上長出。我還注意到,一處已經解構的房屋的斷墻上,一株幼小的泡桐已穿過木柱榫頭的空隙,正努力探向傾斜的天空。眼前的景象,仿佛久遠年代地震后留下的遺跡。
沒有坍塌的,也已十室九空,剝蝕的、黃褐色的木門緊掩。鵝卵石(已被磨得異常光滑,反射著蒼白的日光)鋪就的陳舊老街呈S形彎曲延伸,空寂,就像歲月陳設的一道虛假布景。很久,老街盡頭有一團黑影無聲無息地蠕動著、消失。
某個黝黑的木樓房內,一位老者蓋著薄被還在躺椅上睡著,他寧靜得仿佛進入了另一個幽冥的世界。冷清街道上偶爾響起的腳步聲,沒有驚擾他的幽夢。
一只黑白相間的貓,跳下窗臺,在街心的青石板上停住,驀然回首,久久凝望,黑洞洞的雙眸閃射著詭異,似乎在它身上,依附著某個逝者的陰魂。
頹敗、蒼茫、空洞、沉寂、悲涼……,深秋的黃昏,我所置身的,是一條死亡之街、腐朽之街,或是老街的殘骸,我能強烈地感受到彌漫其中的、濃厚的死亡氣息。這種氣息還來自張貼在木門上的喪聯,眾多的青色或白色、新鮮或褪色的喪聯,觸目驚心:
綠水青山悲去跡,落花啼鳥泣斯人。
章渡,古稱漆林渡。涇縣志載:漆林渡即章家渡,往昔繞岸有漆萬樹,因斯得名。章渡已有千年歷史,唐時即在此設埠置州,轄三縣。唐代詩壇浪蕩子李白游歷涇縣,在章渡留有《早過漆林渡寄萬巨》等多首詩作:“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煙橫積素”、“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回。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后來”。依靠著青弋江,元明時期,章渡一度成為皖南山區通向蕪湖、南京、上海等地水上交通線上的重要埠頭(青弋江邊,尚存“轉運道”石碑),也是涇縣第二大商埠。清咸豐年間,清軍與太平軍曾在此鏖戰,古鎮毀于兵燹,此后重建又曾遭火災。章渡鼎盛時期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酒肆茶樓遍布,四方商賈云集,物產豐富,是皖南山區重要的商貿集散地,彼時,老街兩邊的店鋪鱗次櫛比;菜館、飯莊、旅店、澡堂、木匠鋪、竹器店、鐵匠鋪、五金店、醬坊、油坊、染坊、槽坊、布店、米行、黃煙店、南紙店、理發店、胭脂店、印書局,應有盡有(鎮上還留有一處廢棄的木榨油坊)。如今,數華里的曲折老街,只有街口殘存著一家開設了80多年的中藥鋪和一家理發店。
老街身邊,清澈的青弋江依然峻急流泄,不舍晝夜。
滿腔血淚寒天哀,一曲哀腸凄風悲。
1939年2月,從黃山太平沿青弋江順流而下的一葉竹筏停靠在章渡古埠,從竹筏上走下來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在古鎮茶樓“得月軒”會見了葉挺、項英,并騎馬前往4公里外的新四軍軍部所在地云嶺。自1938年8月新四軍軍部移駐云嶺,新四軍總兵站遷至章渡古鎮的董氏大夫第內。兵站機關人員達60余人,分設軍實、糧秣、行政三科。兵站的物資運輸依托青弋江的黃金水道,發揮了巨大作用,軍用物資輾轉抵達寧波、紹興、廣東、武漢、長沙等地。1938年,兵站接運來往人員五、六百人次。同年,新四軍在章渡設立了中共涇縣縣委,機關設在上街頭(今遺址尚存),章渡成為地方抗戰的政治中心。
嚴親已去恩未報,慈懷不留孝難行。
老街一側沿江臨水,臨江那一排蜿蜒的吊腳樓俗稱“江南千條腿”或“吊棟閣”,木質樓閣分前后兩進,面街的三分之一坐落在陸地上,后進三分之二部分懸空于青弋江上,鋪木地板,每間以6—8根碗口粗的木柱伸入江中支撐。閣樓人家前店后宅,“開門上街,推窗見河”,富有江南水鄉的情調。近百間“吊棟閣”相互依靠,密不可分,站在河灘遠望,林林總總的支柱宛如密密麻麻的雙腿,故名千條腿。在興盛的年代,入夜時分,百家燈火輝映江中,閣樓似一連串的燈籠,所以又稱“吊燈閣”。如今,雖然吊腳樓整體上還保持著昔日的架勢,但已經黯淡、蒼白、陳舊不堪,不少木閣已歪斜、斷裂、破損,似乎只要輕輕一推,它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般無聲倒下。因此,它又像一具死亡了的、正在朽蝕的千足之蟲,它的內部已經空了——雖然還寄生著一些人家——我曾走入其中的一戶,一個老者緩緩起身迎接我的到來,他有點茫然無措,對我提出的問題,他一律回答:“有三個房間。”地板的縫隙里,透出青弋江銀白的粼光,踩上去微微震顫。臨江的方形木格子花窗開著,收容著青弋江、沙洲上的綠樹和遠處的曠野。
老街通向青弋江有六處下河石砌臺階,有些經過人家閣樓的底下。昔日舟楫往來的江面,如今已收縮變窄,變成了一條清溪,全無“漏流昔吞翕,沓浪競奔注。潭落天上星,龍開水中霧”(李白所見)的意境,更沒有了點點帆影,只有一個農婦蹲在溪邊洗菜。遠方,是一片漠漠的平林;寬闊的河灘上,臥著一頭水牛。不知何處有挖掘機正在作業,嘈雜的“扎扎”聲回蕩在靜謐的黃昏。
章渡古鎮的衰落,應該源于水運的衰微。1960年,上游的陳村建起了陳村電站,青弋江的水流量大減,加之水運被更高效的陸運所替代,章渡一落千丈。青弋江,這支奔流的藍色血管慢慢淤塞,章渡隨之黯然失色,慢慢呈現出病態的蒼白。
雨中竹葉含珠淚,雪里梅花戴素冠。
回光返照的夕陽把小鎮籠罩在一片迷蒙之中,夜色出動,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章魚在街面和老墻上伸展。幽深的老街依然闃寂、空蕩,在一種愈加濃重的驚悸氛圍里,我快步退出這個屬于往昔的、夢幻般的境地。似乎聽到過隱隱人語,但當我回首,依然不見一個身影,只有一排排閱盡人世風霜的褐黃色木板門、空空蕩蕩的卵石街道和無聲肅立的灰暗墻壁,在暮景里無限凄涼。一群相互追逐的麻雀,一陣風似的掠過,像在寧靜的水面驚起漣漪,但隨即寂寞如初。
轉過街角,我瞥見一叢不知名的粉紅色花蕾怒放著,與暗淡的老街構成鮮明的反差,這使她有一種不真實的、妖冶的情態,似乎她是某種化身:她的前生,應該是古鎮的某個女子。
抬望眼,那只鷹,依然在老街上空回旋,整個下午,它好像都在那兒,它似乎在空中守望。它守望著什么?
再見,章渡!當我夢游一般踱出老街,走回現實世界的時候,不經意間,卻又看見了一副白色的對聯:
身去音容存,壽終德望在。
穿過“涇溪古鎮”的牌坊,現代商業街上同樣恬靜,低矮、空蕩、冷清的街道后面,是藍山的黑色剪影。夜晚已徐徐降臨皖東南大地,我們要抵達的,是青弋江上游那泓著名的古潭,它在唐詩里波光搖曳,已經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