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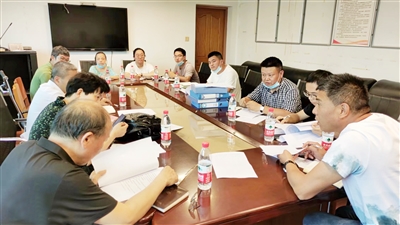


烈日當空,工人們就著棚下的陰涼小憩,有的已經打起了盹,景志祥貓在一旁,在手機里打出一行行字。利用午休兩個小時零零碎碎碼上一千多字;下班后晚七點準時坐在電腦前,趕在九點前梳理成篇;第二天五點半起床,六點坐在電腦前開始新一天的創作,八點出門去上班;遇上開會前等待或是碎片的幾分鐘,就把幾天前的稿子翻出來重新看一遍,順手改一改……一頭忙著項目監理工作,一頭把玩著自己的文學愛好,自2009年從長江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水利工程建設專業畢業,入職浙江興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這樣雙軌并行的快節奏狀態已在景志祥生活里持續了13年。
讀書破萬卷
“今年已經出了兩本,正在寫第三本,現在手機好,隨時隨地可以寫,看書也很方便。”景志祥說。遙想兒時,他的家鄉在湖北黃岡一個偏僻小村,村里極少有人識字,上了學才知道當地特產是“黃岡密卷”,很多人靠著它“鯉魚跳龍門”。那些跳不出龍門的,趁年輕,紛紛涌進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浪里淘金去,帶回來一打打厚厚的書,村里人都傳著看,景志祥也跟著讀。那書里不是之乎者也,也不是數理化公式,里面全是江湖上的故事,起初是金庸,后來是古龍。那時候,景志祥剛上小學,這些書上很多字不認識,也沒有拼音,他就這樣半懵半猜地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買書太貴,能借到的書不多,好在很快村上的集市里開始有了小書攤,父母平日給的零花錢,他舍不得買吃的玩的,全花給了那小攤販。他偏愛歷史題材,正史、野史、連環畫都看,在小書攤前一站就是半天。
這份如饑似渴不知不覺間仿佛長進了他的骨髓里。初中讀賈平凹、路遙、沈從文,高中看《讀者》《青年文摘》,直至后來上了大學,室友們相約K歌、打游戲,他一人躲進了圖書館,礙于借書量的限制,寢室里閑置的四張借書卡全進了他一人的口袋。那樣日夜啃讀的四年里,他讀懂了文史不分家,讀懂了行文造句的章法,讀懂了從時間長河里走來的千千萬萬的人生,讀懂了書里藏著的豐盈世界。
可是,景志祥并不是個作家。自初一時他就不間斷地給雜志社投稿,延續到大學畢業,無一例外石沉大海。這種挫敗感于他而言并不陌生,早年“黃岡密卷”和他也沒有眼緣,奧賽第一道雞兔同籠題就把他難住了,同班數學小天才平日吊兒郎當照樣考到了第一。“人生就好像一趟旅程,有的人先上車,有的人后上車,只要我在車后面不停地走,最終大家的目的地可以是一樣的。”多年以后,景志祥發現,這份骨子里的愣勁兒是上天給的巨大寶藏。
下筆如有神
那年,景志祥剛畢業,隨項目部駐扎在衢州市一個偏遠的山村,村里人外出只有一趟公交,早晨六點半下山,下午三點半上山。到了周末,景志祥就下山背一摞書回來。山里人睡得早,剛過七點,萬籟俱寂。大山頂上的一盞孤燈把書卷照得昏黃,燈下的青年在漫漫長夜里啃食著他的希望與彷徨……
就在那一年,他投稿的一篇圖片新聞被《衢州晚報》采用,這塊小小的“豆腐干”給了景志祥極大鼓舞。他領了50元稿費,請大家吃了一頓300元的大餐。席間,一眾人推杯換盞,暢聊著未來的作家夢,還有人聊及新興的微信公眾號。為什么不換一種方式投稿呢?在大家的鼓動下,他很快注冊賬號。
智能手機的普及,讓網絡文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期。一次尋常的出差,火車上有人隨手塞給他一本《誅仙》,他讀完了說:“這個我也能寫。”后來又上網讀完了《鬼吹燈》,他隨即在起點中文網以筆名“一景之月”開始了《逍遙江山》的持續創作。他把心愛的西湖、史上有趣的人物洋洋灑灑編織進他的故事里。持續五年,日更六千到一萬字,培養他與筆尖的親近感,粉絲的追捧更更給了他創作的動力。《逍遙江山》一度登頂歷史題材類月票榜榜首,景志祥也隨之收獲豐厚的稿費,并斬獲2013年行業劇大賽優秀獎、2016年年終盤點優秀獎。
2017年,《逍遙江山》創作完成。停筆的一段時間里,景志祥反復讀著《編舟記》,開始思索自己未來的創作走向。他重拾微信公眾號,回歸傳統文學,在與一眾雜志編輯的反復交流中漸漸觸摸到了自己在歷史散文創作領域可能的定位。“一騎紅塵妃子笑”,那策馬而來的人是誰?他又有著怎樣的傳奇故事?朱元璋“空印”事件背后又有著怎樣的巧合?這些于經年累月的海量閱讀中采擷而來的鮮為人知的小人物、小故事成了他筆下源源不斷的創作題材。很快,他的微信公眾號被一眾編輯關注,他也頻頻收到《青年文摘》《瘋狂閱讀》《百家講壇》《金秋雜志》《國家歷史人文》等雜志的約稿。
“現在新人出書,版稅一般在6個點,有聲版權一般三年期限……”十余年的網絡文學發展讓版權運營日趨規范有序。景志祥的作品也陸續被喜馬拉雅等平臺購買有聲版權、影視版權、衍生版權。

看婺城新聞,關注婺城新聞網微信
<sup id="ecicy"></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