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張波(杭州華文影視公司編劇):“《千秋令》有點像散文詩”
張波開口即道“《千秋令》是個了不起的事情”,這個戲具有時代的意義,符合時代潮流,且是個非常新潮的戲。有人質疑,地方上的東西怎么推廣到全國去?張波認為,越是地方的,越是中國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反而不成其為問題。《千秋令》不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而且它著眼于老百姓的利益,講的是縣令宋約如何為百姓做主的故事,因此,張波認為抓住這一題材,恰恰說明作者是“很有眼光的”。
就劇本本身而言,《千秋令》自有瑕疵。“這究竟是一個什么劇?是歷史劇、歷史故事劇、歷史傳奇劇,還是整一個傳統戲?”張波說,“風格要講清楚,我主張這是一個歷史故事、歷史傳奇,新編歷史故事劇或者新編歷史傳奇劇,都可以。但定調要定準。”這樣,傳統戲里面作為入頭戲的套路要清理掉,比如自報家門,在有字幕的情況下,無須多此一舉。
背景是歷史的,故事是傳奇的。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應該避免,例如“大明天子憲宗皇帝是也”,憲宗是廟號,屬于死后追認。汪直是有明一代蠻出名的宦官,攻于心計,在《千秋令》中就過于臉譜化了。“(角色)既然出來了,就要像個樣子。”張波說。然后,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大膽發揮,盡情創造。
“宋約在湯溪當縣令,立意為民,可以參考當年跑到廣西當縣令的于成龍,人家的衙門只有三間茅屋,喝酒的時候,讀唐詩下酒。窮到這個程度,廉到這個程度,寫宋約,就可以往這方面靠攏。”
劇作者洪增貴花了三年的時間寫《千秋令》,這一點讓張波很感慨,他說“戲劇編劇含金量最高、最苦,但稿費也是最低”,他們當年招進戲劇寫作班的大學生,到現在沒有一個從事戲劇編劇工作,可見一斑。但《千秋令》的人物形象沒有進去,故事結構略顯脫節,以致看每一段都有意思,看一整出戲則缺少連貫,張波說“倒是有點像散文詩”,劇本的關鍵在故事,既然花了時間下去,必須下點功夫進去。他還給洪增貴支了一招,牽涉到老百姓容易誤解、引起矛盾的時候一律回避。
“這出戲,題材好,一定要抓,這不僅是促進婺劇的一個本子,與提高婺城的知名度也大有關系。”張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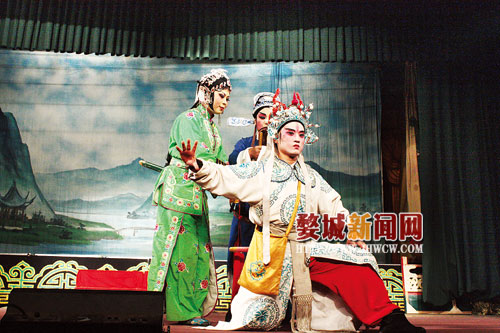
曾昭弘(浙江藝術研究院著名劇作家):
“與魯迅寫的社戲差不多”
曾昭弘在虹路看完戲回來,很是感慨,“好像看到了魯迅先生寫的社戲一樣,中國傳統文化就在這里。”盡管文化被折騰了好幾十年,根性在,春風吹又生,照樣能夠活過來,照樣能夠繁榮起來。“我看花抬頭,那感覺真美,真好。”曾昭弘說,“這種廣場藝術,讓我大開眼界,老百姓像過節一樣,臺上的演員,一招一式,功夫不比專業演員差,比越劇里的專業演員還要強。”
當他聽說劇作者洪增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連聲稱贊“了不得”,他說:“那些大學里專門學戲劇的人,沒有一個像你這樣搬上舞臺的。
曾昭弘提出,要寫戲劇,先編故事。只有編一個男女老少都愛聽的故事,之后,你的戲劇才有人看。因此,曾昭弘開出一張妙方,“立主腦,減頭緒,清脈絡,密針線”,所有與會專家一致叫好。戲劇要開門見山,要說什么說什么,不要拘泥于事件,人物一旦塑造好,事情講清楚,一個好的戲劇自然而然就出來了。
方圓(原浙江婺劇團編劇):
“干脆以銀娘
省親為主線”
方圓對“銀娘”一事,認為不宜拔高。銀娘不過是“坤寧宮宮人”,恐是小名喚作銀娘,而非宮中娘娘。從歷史傳說可講,從歷史記載則不可講,至于太子見銀娘那一幕,更是離奇,東宮太子僅有一個,銀娘豈非成了皇后,若是如此,如今銀娘的家鄉——寺平古村也該不是現在這般面貌。所以,太子這一出,去掉為妙。
但銀娘的事不免啟發了方圓,一個中心事件,必須依托于一個情節才能發展下去。既然銀娘可以叫娘娘,不妨就這么叫下去。如何串聯整個故事,如何推動劇情發展,如何激化正反矛盾,恰恰都著落在銀娘身上。“我們不妨就以銀娘省親為主線,這就有戲好做了。銀娘要回湯溪娘家來了,那是大事,看看《紅樓夢》就知道了,甯妃省親那是不得了的,國家要花多少億銀子,大觀園要重新造過。”方圓說。修路蓋屋不可避免,但湯溪又是一個窮地方,宋約只能向皇帝要錢,皇帝也給錢了,但宋約把錢用來救濟百姓,這就有了一個大沖突,欺君。地方勢力抓到了宋約把柄,聯合朝中勢力,意圖致宋約于死地,再把《千秋令》中能與此線相配合的段落,相互穿插,故事自然就豐滿起來,這個劇本就有了羽翼,可以振翅烈烈了。

看婺城新聞,關注婺城新聞網微信
<sup id="ecicy"></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