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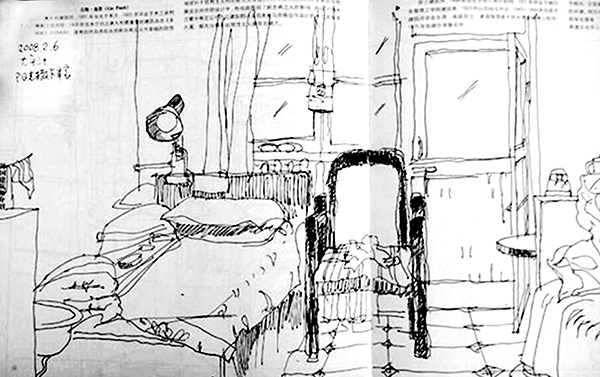

���������Y����ڼ�(j��)��(j��)��������1938�����ںӱ����������I(y��)�����A��W(xu��)����ϵ(1958����1964)�����α����н����O(sh��)Ӌ(j��)�о�Ժ���ν��������B�����O(sh��)Ӌ(j��)�����������������С����c�@�������c�꡷�����c�ۡ������������ȡ�
������į���A�ˮ���(sh��)��
����
�������o���x���xӾ�����ݼĵăɱ���(sh��)���W(w��ng)�j(lu��)�r(sh��)���҂�?n��i)���x��(sh��)���͡�˼������������(d��ng)���Ї�(gu��)�о���ʷ�φ�(w��n)�}���r(sh��)����ֵ�����^(gu��)��ĸУУ�c�����겢���Ǵ�c������ʮ��Ҳ�����壬���s���Һ���ͬ���ʮ��(g��)ͬ�W(xu��)�����صĮ��I(y��)��ʮ���һ�ꡣ��������һ��(ch��ng)�治�Ľ��ڌW(xu��)���ؾ۵ęC(j��)�����Լ�Ҳ���d��(xi��)�ˎ�ƪ���ӣ�����һ��С��(c��)�ӣ�����ͬ������һ��(g��)���룬��(du��)��ȥ��ͬ�W(xu��)��Ҳ��(du��)�@�Κg�ۡ����W(w��ng)���͡�˼�������ѹœ��ƪՄ�����(gu��)֪�R(sh��)��(�����������A)���ˣ�߀�f(shu��)����ʮ�־���Į���(sh��)��������
����һ���������W(xu��)У�����ݱ�Ľ��������˳��У���̤�����A��У�T(m��n)����h(yu��n)̎�����A�W(xu��)�á��Ҵu��������W(xu��)�r(sh��)ϵ�^��ϵ�^һ���Ђ�(g��)������ϵ�D��(sh��)�^�����@�������J(r��n)�R(sh��)�ˮ���(sh��)�����ˣ���(l��i)ȥ�Ҵ���ô���ώ���߀�в����������Ձ�(l��i)��
��������ϵ�����A��W(xu��)����һ��(g��)���p��ϵ��һ��������Ž�����ϵ��Ľ����ƺ��](m��i)�����L(zh��ng)�ڮ��ģ���ֻ�LjD��(sh��)�^һ��(g��)��ͨ�^�T�������p�ώ���1949��ǰ�w���ڣ����H�еطQ������(sh��)�������鮅�ϡ����W(w��ng)����(sh��)����һƪ�f(shu��)������(sh��)��������2014�ꄂ����ġ��ݾ���ӛ������������Ǯ��ϵ�������ӛ��̫���@ϲ�ˡ�
����ԭ��(l��i)�@��һ�������^(gu��)����ʮ����ɮ�(d��ng)���˾�����ļ��ӣ���(sh��)�м��ˮ���(sh��)������1930�����1940����l(f��)���^(gu��)����ӛ������(l��i)��(y��ng)��1949�����������Ψһ�Ą�(chu��ng)���������ˡ����Ȳ�������ȥ�I(m��i)��(l��i)��һ��СС�Ҿ��µĕ�(sh��)�����H�����������ꌦ(du��)���������L(f��ng)���ӛ����߀�B�������˼ҵ�������ò��
����һƪԭ�d1957��5��8���Ϻ��ąR��(b��o)�����֣����J���ҵ��ۺ����}Ŀ�С����֏d�������f��֮һ�����Ҳ����f(shu��)�@������������P��(l��i)������һƪ��Ʒ������֪�Ƿ����������o�҂������һƪ���£�����߀�Л](m��i)�й��֏d֮����֮����
�������ҿ��Բ�����ǣ���һ�꣬1957�괺�죬δ��ʽ�l(f��)����ë�ɖ|������������(hu��)�h�ϵ��vԒӛ䛸���֪�R(sh��)�����Ђ��b�������ְW�ˣ�߀���ֲ��^(gu��)���ѵļs�壬���������@ƪ�������ġ�
�����F(xi��n)�ڻ��뮔(d��ng)�꣬���Ϟ���һ����҂�?n��i)�W(xu��)�ˣ�ɵɵ���҂�?c��)�ôҲ���?hu��)���@λ��������ߺͽ����Ҋ(ji��n)���IJ�(li��n)ϵ����(l��i)��ֻ (t��ng)�f(shu��)��Ӣ�ĺã��](m��i)�����f(shu��)�^(gu��)�e�ġ�
���������֏d�������A���½���������������ɽˮ֮�g��һ���ŵ佨�����Ƶ�Ժ�䣬������(hu��)����������������T(m��n)�Ϸ����~�}��(xi��)�ġ����A�@���ׂ�(g��)�غ���֣����V�����������A��������һ��ͬ�W(xu��)��(hu��)����W(xu��)У���^�X�����ڴ��k������(hu��)�h���Ϳͣ��ñ��L(zh��ng)���ֵ����A�T(m��n)��(n��i)�����֏d��(n��i)�ܰ��o��ͬ�W(xu��)�������ɳ��룬���O���L(zh��ng)�r(sh��)�g���������˽���ϵ��(xi��)���ČW(xu��)�������َ����Į�(hu��)�������挍(sh��)��߀�������s���ٱ��Ϯ����������ĕr(sh��)��׃�õ��⾳��
����������x���@ƪ���A�@���f�κ�����W(xu��)�r(sh��)�x����У��������ȣ�������һ��(g��)�r(sh��)���ġ���(zh��n)�춷��?z��)ᳱ���B��Щ�Ȯ������L(zh��ng)���Ļ��ˣ�Ҳ���Ю����@�ӵ�С�Y���{(di��o)�Č�(xi��)���ˡ�
��������Ҳ�������X����ˣ����v��(sh��)�����ι���̩��?du��)��Խ������L(f��ng)�A��ï��һ�����ڹ��֏d�F(xi��n)�������˺��ĉ�����֮�P�hһ�D(zhu��n)�R�ϵ��ˮ�(d��ng)�¡��������c(di��n)��Ƥ�sһ������(j��ng)���f(shu��)�Լ����c(di��n)���ǂ�(g��)�������Գ�Ó�������ḯ�����������t�c�r(sh��)����܉�ı����������nj�(xi��)��������߀ð�����ң��T��(hu��)��菸���(hu��)���f(shu��)ʲô���֏d�ġ������ֺ��ƴ�W(xu��)�ġ���������һ�x��ͨ��һ�}�������ֲ��_(k��i)�ģ���ͳ���(l��i)���˲��ǹ����A��(j��)�Ĺ��̎��������I(y��)���������f(shu��)���㺆(ji��n)ֱ��̫�ǂ�(g��)�ˣ���
������Ҋ(ji��n)�����ϕr(sh��)�������°l(f��)��֮���꣬�](m��i)��һλǰ݅��?q��)W�L(zh��ng)�f(shu��)���^(gu��)�@ƪ���֡��҂���(b��o)�����A�����DZ����@���Ї�(gu��)��һ�Ĺ��ƴ�W(xu��)��(l��i)�ģ��҂�����δ��(l��i)�Ĺ����A��(j��)�Ĺ��̎�������ÿ���挦(du��)�Ĺ��ƈD��(sh��)���M(j��n)ϵ�^������^(gu��)���ǹ��������](m��i)�����P(gu��n)ע�����е��Ŀ���ѣ���ֻ�ǟo(w��)�˺�����(du��)Ԓ�����ˣ���Ҳ�S�¼��ˣ�������ˡ�
������������������΄�(sh��)�����΄�(sh��)�l(f��)չ֮�죬���p�˶�δ�ظ����ϣ��������治�ܿ��������ˡ������A��(j��)�Ĺ��̎��njW(xu��)���K(li��n)�ģ�����f���A�@��(g��)�F��W(xu��)У���B(y��ng)����������Ŀ�������֪�R(sh��)�����ьٷ��츲�صĸ����ˣ������S�M(j��n)�΄�(sh��)�£����B(y��ng)ʲô�ӵĹ��a(ch��n)���x�Ӱ��˴��qՓ��������ֱָ����һ��ǰ߀����(j��ng)��(bi��o)�����T�˵�������̖(h��o)���������ēu�@�����o(w��)�a(ch��n)�A��(j��)�Ľ�����������B(y��ng)�W(xu��)���ɞ�һ��(g��)��ͨ�ڄ�(d��ng)�ߡ�
�����Ǖr(sh��)��ֻ��ĬĬעҕ�����ˣ�����̫�˽⮅�ϡ�ԭ��(l��i)����(sh��)����������˼������ͬ�g��������1900�ꡣ��ԺУԺϵ�{(di��o)����������������Ո(q��ng)������ϵ�D��(sh��)�^�ġ�
����1994�걾�ˮ��I(y��)��ʮ��r(sh��)�������AУ��ͨӍ���������һؑ���W(xu��)�����С�ģ��@�ӌ�(xi��)���ϣ�
�����������@�ݹ�������������IJ���ɡ���������ɲ���(l��i)�Ļ�����Ϟ�ʲô���ٌ�(xi��)�c(di��n)ʲô���g�c(di��n)ʲô���@�Ӳ��Ǹ������xҲ��Ȥ���ͬ�W(xu��)�ͮ����f(shu��)���������҅f(xi��)��(hu��)����ĕ�(hu��)�T�r(sh��)������ЦЦ���ͽ���(hu��)�M(f��i)�����(hu��)��˴��׃����˸е��������W(xu��)�������Ѳ��ϕr(sh��)���ˣ���������֪֮���ģ����������������Ҳ�ښvʷ�����^�����˵�ӛչƷ���v��Ĺ������
������1960�������(j��ng)��(j��)���y�r(sh��)�ڣ��W(xu��)У��p�p�W(xu��)��ؓ(f��)��(d��n)���W(xu��)�r(sh��)�����^�ɣ���ϵ�D��(sh��)�^�ֺ�ů�ͣ�ͬ�W(xu��)����ϲ�g�C������U���ο���������g�[�ͷ��ʲô��ֻҊ(ji��n)���Ͽ����o�o���ڳ���(xi��)������(sh��)���Ŀ�Ƭ�����ϵ���ώ�У��ĸ壬߀��(j��ng)���������������ڼ��ϳ���(sh��)������������Щ�µ����^(gu��)�ڵ����Ľ����s־����?y��n)��҂����Z(y��)�W(xu��)���Ƕ��ģ���Ҳֻ�ǿ��D���Һý����s־����ĈD��ï��߀�f(shu��)��������߀��(hu��)���D�R(sh��)�֡��Еr(sh��)�������dȤ�ĵط�������֪����һ�c(di��n)��ֻ���韩һ�������˼ҡ�����(du��)�҂��@Щ�Ͱ��W(xu��)��Ҳ�����ģ������t�ͣ����f(shu��)�������������ƣ�һ�ڝ��ص�ɽ�|�����������˶�������˼�ٶ�һ�δ�_������
�������ڌ�(du��)���������Ă���u������(l��i)���Ҿ�Ȼ�ڌW(xu��)У��D��(sh��)�^Ŀ䛏d�Ŀ�Ƭ�����ҵ����ꮅ��ɢ�ļ��ӵĿ�Ƭ�����ǽ��(l��i)�ˡ�����(xi��)�@ƪ���r(sh��)����ôҲ�벻���(sh��)���ˣ����(l��i)���ڡ��ݾ���ӛ��һ��(sh��)���һ�(l��i)���С�����(m��ng)������������ƪ����ӛ��һ��֣������f(shu��)����ϯ�g�����o������һ��Ԓ������ͣ�磬��˶��ٳ���һֻ��������������Ĭ�SȻ���ϡ�
�������όW(xu��)�r(sh��)߀���f��(sh��)������һ�����s־��(sh��)���Ͽ����^(gu��)����(sh��)�����������(gu��)��Ӎ��a(b��)�ף���ij��������Ʒ�����@���u(p��ng)��ij���ĺ����š���ӛ���� (t��ng)�f(shu��)߀�ǿ��ģ���������Q�@����ֽС���(b��o)�ʱ�����
�����ݾ���ӛ��Ҳ�����ߵ����º�Ȥζ��S�����f(shu��)��(sh��)ֻ����Ȥ�͟o(w��)Ȥ�ɷN����ӛ��Ҳ�����@ô�f(shu��)������(sh��)����������ӛ����Ȥ��Ϭ�����۹⣬��Ƥ�����ģ����f���C��
������У�r(sh��)���ң���������ֻ���J(r��n)�棬��Ҳ��į��
����1980��������X(qi��n)���������ġ��F(xi��n)��������ӛ�x�����x���ˮ������ġ��������ˡ���ӛ��������H��ʮһ�q��(y��ng)Ƹ��������Ӣ�ķ��g��ͬ��������A��W(xu��)�D��(sh��)�^�ϰࡣ��ӛ�M��(xi��)�@�����_˹߅�ǵ��L(f��ng)�飬�o�������˽�����ǰ����(d��ng)��(hu��)�档�ҿ��@����(sh��)�r(sh��)����������(sh��)�İ낀(g��)���o(j��)ǰ����Ʒ߀�](m��i)�б�����ӛ��ʮ�ָп���
����1990�������������������������(�F(xi��n)�����ҹP�µı���)�����1949��ǰ��λ���ҵ�ƪʲ�������Ю��ϵġ���ƽԒ��ı������������������f(shu��)�������DZ���Ԓ����Ҳ�����(hu��)�f(shu��)������������ˣ�������һ��Ψһ��׃����һ�ڝ��ص��z�|������Ȼ�����s����(d��ng)�،�(xi��)���������Z(y��)��Ъ���Z(y��)�ͺ�ͬ��������(l��i)�ġ������ӡ�֮����~�����F(xi��n)��һ��(g��)�������L(zh��ng)�ı����˶�δ�،�(xi��)�ó���(l��i)�ı����˵��Ը����ѡ�
�����Һ�Ȼ�������όW(xu��)�r(sh��)ֻҊ(ji��n)������B(t��i)ĬĬ����ϣ���ܸQ���S���IJ���(��i)����ă�(n��i)�����磬���](m��i)�С������źܶ�ܶ�ֻ�Dz����ĵ���̎�T�ˡ�
������������(hu��)���y����һλ��H��ʮ�q���˱��˷Q��ij�ϣ���Ҋ(ji��n)����(sh��)��������(d��ng)�r(sh��)ĩ����˥�Ę��ӡ����@�^���Ǽ��������������һ��(g��)�挍(sh��)���ˡ����p�r(sh��)ԭ����һ��(g��)�o(w��)���Y�v�ĈD��(sh��)�^С�^�T���ԏ�(qi��ng)��Ϣ����Ҳֻ��һ��(g��)�F���ˡ����ڈ�(b��o)������(xi��)����Ӎ�W�£���������(du��)�ČW(xu��)�ğ��(��i)�Ͳ���ҕ�硣�f(shu��)���挍(sh��)��ָ������������������h(hu��n)���YӍ�l����ͬ�r(sh��)������?gu��)��ں��Ӷ࣬�@�c(di��n)���(��i)�f(shu��)����߀�o�����кܺõ��a(b��)�N��
�����x�_(k��i)�W(xu��)У��͛](m��i)�Ю��ϵ������ˡ����A��(d��ng)�yʮ�������^(gu��)���L(f��ng)Ѫ������ӣ���У�c�r(sh��)ż��������δ֪��������ζ��^(gu��)�ġ����Ǻ�����֪������(sh��)�ı�������Ѹ�����ɡ�����(d��ng)Ȼ��ԭ�IJ���(hu��)�����ˡ���ֻ֪Ƭ��ֻ�Z(y��)�����^(gu��)�õ���Ǵ��治�����������ض����ˎ�ʮ������ˣ���ֻԸ�������ĸ���δ�ɴ˶��ܿࡣ
������̹�����ڴ��ϡ��ن�
�����յ�����һ�ڡ��f(w��n)���s־�����ڴ��ϡ��ҕ�(sh��)�����ߵ������������ҵ�ע�⣬Ŷ��߀��(hu��)��һλֵ���˂��ؑ����ˣ�Ҳ����̹����?y��n)龎�ߺ������ҕ?sh��)�߾�δ��ֻ�ֽ�B���r���@���ֳ��F(xi��n)�ڷǽ������I(y��)��һ�������s־�ϡ�Ȼ����(d��ng)�ҷ������(y��)��Ҋ(ji��n)��һ��Ę����Ϥ����Ƭ���Ż��^(gu��)���(l��i)���@�����҂�ʮ�־��ص���̹���������҂����ώ���
����1950���ĩ��1960���������ֻ��һ��(g��)��ͨ�����W(xu��)���I(y��)�ČW(xu��)����������ο��(d��ng)���ж�ΙC(j��)��(hu��)�� (t��ng)�������v�n�ͽ����x�o��(d��o)����Ҳ��ڛ](m��i)��ץס�C(j��)��(hu��)��ϧ�W(xu��)��(x��)�C(j��)��(hu��)����W(xu��)�r(sh��)������������ӡ���ѽ�(j��ng)��������ˣ�������ʮ��ļҕ�(sh��)����?y��n)����һ��(g��)�������������X(ju��)���b�h(yu��n)�ˡ���ֵ��ǣ��@Щ�ҕ�(sh��)ɢ�l(f��)��������ʧ�����(gu��)��Ϣ�Ŀ���(sh��)֮�L(f��ng)���ڽ������x�����ֱ�������(f��)�
�������ڴ��ϡ����������ҕ�(sh��)�ļ��\���x�����ӡ�C�ˡ��������ˡ��@���Ԓ���ҕ�(sh��)����(d��ng)��δ���b�뵽�պ��(hu��)���@ô���o(w��)����˸Q��������ֱ�ʣ���¶����˹�r(sh��)˹�ص�������������(hu��)�䏈���o(w��)��������?y��n)��@�ӣ��Ҳ��X(ju��)�����M(j��n)���ˌW(xu��)���r(sh��)�����R(sh��)�������r(sh��)�����������뵽���ԬF(xi��n)��(sh��)���F(xi��n)���ĸ��S���ă�(n��i)�����硣
������(d��ng)�꣬��һ��(g��)߀δ���T(m��n)��������(����Buiding)�ČW(xu��)������ô�͌�(du��)�������е��dȤ�أ����v�n�ͽ�Մ�Ŀ����Һ�(��һλ�����u(y��)��һλ���ҵ��f(shu��)�������Z(y��)���ٲ���)��֫�w�䏈����ǻ���{(di��o)�������ܳ�һ��(g��)�v�_(t��i)���������@һ��Դ������(du��)�̌W(xu��)�ğ��(��i)��ҲԴ������(du��)�W(xu��)�ӵğ��(��i)����߀ע����������c����ͬ��һ�c(di��n)������Ԓ�Z(y��)�Ў��](m��i)�С����β����_������������(sh��)ʽ�Ľ̗l����ֲ�ͬ�ڷ��Һ�һЩ�Ͻ��ڵ��������������������s��
�������ڴ��ϡ��ı����جF(xi��n)���������ٌW(xu��)�ӳ羴�Ľ��������Һ͌W(xu��)����̹��������һ��(g��)�^ȫ�沢�����������˸��������o���ˡ�1950�����1980������(hu��)��׃�£�������Ҳ�ʬF(xi��n)���Լ��IJ�ͬ��������ͬ������������ҕ�(sh��)�r������p�r(sh��)����Ʒ�������ϡ����A�����¡�����������齨���ģ������Ќ�(du��)��Đ�(��i)��
�����ҕ�(sh��)���f(shu��)���������ݽ̵�����(gu��)�����ώ��R�ؕr(sh��)���@�ӵ�Ԓ����Wright�@����������ˣ�֪�������˘O��(���ˌW(xu��)��������)����(li��n)�뵽Ҳ�S�����W(xu��)���⣬����(sh��)��Ҳ��һ��֪����̹�����I(y��)�ɾ͡��@�o(w��)����һ��(g��)���˚J���ϲ�g���ˣ���Փ���Ǹ����еģ���Փ֪�Ե��˶��٣�����Ҫ����ϧ���ǚvʷ�](m��i)�����o��̹����̫���r(sh��)�g���������M(j��n)�������������Փ�r(sh��)���������Ѳ������꣬߀��æ�������������ѡ����Ҵ�ȥ��(gu��)���ִҴҷ���(gu��)�����Ǟ����@��(g��)����һ�Ⱦ��ǎ�ʮ�ꡣ
����1958���^��W(xu��)�r(sh��)��һ�꼉(j��)�����](m��i)��У�գ�Ҫ����������ϲ��|(zh��)�ؿ����tɫ߅���(n��i)�˶������ׂ�(g��)�����w�֣����A��ͬ�W(xu��)���҂�������ǰ�h����Ƭ����ÿ������^(q��)�ܵ��|�^(q��)���֏Ė|�^(q��)�s�����^(q��)����
����һ�꼉(j��)���n���ǻ��A(ch��)�n��Ψһһ�T(m��n)���I(y��)�n�С�������Փ���������������v�ڡ���������Փ����һ�T(m��n)�����n�����˘O�ٔ�(sh��)�ܼ�ͥ�I(y��)Ӱ푌�(du��)�����������c(di��n)��������ģ���ͬ�W(xu��)��������(x��)�����������W(xu��)����ʲô����������Ҫ�W(xu��)����Architecture������ָBuiding��
����1958����һ��(g��)���������ȫ��(gu��)�l(f��)��ʲô�£��W(xu��)У����ʲô���������F�����k������������������d�o(w��)���Y�������߰�ͬ�W(xu��)ȥ��ˮҎ(gu��)���O(sh��)Ӌ(j��)������Ĺ��a(ch��n)���x��סլ����ʳ�á��f(shu��)�乫��Ԓ���������A̫���ˣ�ÿ�(xi��ng)���(d��ng)����һ����ȥ�㣬���@�ß�����ˡ��䌍(sh��)��ͬ�W(xu��)�ʹ֕r(sh��)�g��δȫ���Ƴ�Ҏ(gu��)�ͽ�������
������(d��ng)Ȼ������ϵ�_(k��i)ʼ���С��������ēu�@���͡���(g��u)�D�ǽ������Ŀ��ұ��I(l��ng)�����f(shu��)������̹�����������@�ӵĴ����_(k��i)�n�ˡ��_(k��i)�����x�ظ��Vͬ�W(xu��)���W(xu��)�����Ǟ��˸�ʲô�أ������Ԇ�(w��n)�Դ��췿�ӡ��҂��@Щ߀δ���T(m��n)�ģ���(d��ng)Ȼȫ�P(p��n)���ܡ��҂�Ҳ��֪�����y(t��ng)�Ľ�(j��ng)�佨���W(xu��)��ô�v��Ƭ��ֻ�Z(y��)������ۺ������ڴ��ֈ�(b��o)��ϵ��������������A�W(xu��)�á��T(m��n)�d����������ɫľ�����Ͽմ����˸߰�ͬ�W(xu��)�Ę�(bi��o)�Z(y��)�����(li��n)����ժ�ԶŸ�Ԋ(sh��)ʥ�ġ����ÏV�Bǧ�f(w��n)�g����
�����r(sh��)���낀(g��)�����o(j��)�ˣ���?z��ng)]���l(shu��)ȥ��(zh��ng)�q�@��(g��)�f(shu��)���Č�(du��)�e(cu��)�����f(shu��)����Ľ����W(xu��)�ӣ���(d��ng)�����е�һ��(g��)�f(shu��)���С����ȫ��(gu��)����Ľ����X(ju��)���@���Q�������Եġ�������ϵ��ij���꼉(j��)һλ�W(xu��)�ӣ�Ҳ�S������ǰ߀������Щ������ߡ��X(ju��)������X(ju��)���ϰ�������Ľ����Ю�(d��ng)�������w���ӆ�M���W(xu��)�������g��һ���ώ�����(d��ng)�������W(xu��)�ĴT���������f(shu��)�ˣ���(du��)�������^(gu��)���Uጾ������f(shu��)�ˣ������@��(g��)Ȧ����](m��i)�ж����˿����x����
�����ص�1958����������������Ԟ������@ô��ģ�߀�����@ô��ģ������̫��������Ĭ�ˡ��ҵ��Ǐ�����(d��ng)������ʮ���1948��˽���У������������Ķ���(��i)����ź��ǻۡ����ҡ����������������(��i)���(gu��)�����(��i)������Ҳ���(��i)���ČW(xu��)����߀�Ќ�(du��)�Լ��������P(gu��n)��(��i)���������@���v�ġ�һ�N�x���ǙC(j��)�����o(w��)�Σ�협�(y��ng)���Ӷݣ��@�џo(w��)�ɲ�ԃ��
����������@��(d��ng)��һ��(g��)��Փ��һ��(g��)���ص���Փ����Ҳ���o(w��)��������(d��ng)�҂���(gu��)���M(j��n)�������o(j��)���������r(sh��)�ڵ�ʮ���(l��i)��������ӛ���˶Ÿ���Ԋ(sh��)���ٷ�֮�˾�ʮ�Ľ������Ĺ�����סլ�O(sh��)Ӌ(j��)���ϰ��ղŲ�����ʲô�O(sh��)Ӌ(j��)���ֻ���з���ס����Ҳ�С�
����߀�в����ٷ�֮ʮ�Ľ������ڸ�ʲô�أ��������ܲ������O(sh��)Ӌ(j��)һЩ�˿����������۵ġ�ƽӹ�������� (t��ng) (t��ng)�I(y��)����ʿ���f(shu��)�ˣ��������Ԟ��ڄ�(chu��ng)�£��sԭ��(l��i)�ڿ�¡��Ҳ�С�ԭ��(chu��ng)���ģ��ϰ������ڿ�����ȥ�ˣ�ǰ���ò��ǾW(w��ng)���u(p��ng)����ʮ���������������M(f��i)���|(zh��)�YԴ�������YԴ�治���ό�(sh��)�췿�ӡ�
������������@�ӣ��Ҍ�����������̹���������R(sh��)�Ľ����^��ֱ�X(ju��)��ӳ(�@��1950��1960��������������Еr(sh��)��(hu��)�в���(j��ng)����@¶)�����罨���ɸɃ���đ�(y��ng)��(d��ng)��ְl(f��)�]���W(xu��)�Ͳ���������(�(j��ng)���֫�w���_(d��)����������ǰƽ���p�ۑ������������Ȅ����ǽ�����ˮ�e������(d��ng)��](m��i)ʲô���HҊ(ji��n)�������������������R�ص�����)���������ЙC(j��)�ģ����c�h(hu��n)���P(gu��n)ϵ�����ط��������@�c���ڮ���(gu��)���ܵ��ǬF(xi��n)�����x�Ľ��������W(xu��)���R�ش����P(gu��n)�������������(hu��)؟(z��)�θеČW(xu��)�ˣ���ͬ�r(sh��)Ҳ�J(r��n)�����������(hu��)���̣���ӳ���ǡ����������������������ȥ��(gu��)�r(sh��)�����У��ͱ��_(d��)���@�ӵ��պ�(chu��ng)����(zh��n)��(��Ҋ(ji��n)�ҕ�(sh��)1948��2��9��)��
�����eһ��(g��)���ӿ����f(shu��)���������Ƿ���(du��)�����Г�(d��n)̫����ԭ���Г�(d��n)����ġ����ܡ���ӛ����һ��Ű���������o(j��)�¡���������o(j��)���(du��)�����壬�Ї�(gu��)������e�O��(y��ng)�����W(xu��)УҲ�M���������ӣ��҂��ǂ�(g��)�W(xu��)��߀�R�r(sh��)����һ�Ρ������O(sh��)Ӌ(j��)�����I(y��)���������M(j��n)�Dž��ӑ�(y��ng)���������u(p��ng)�x��(hu��)�h��(l��i)����ȫϵ������B��r���e��(du��)ij���O(sh��)Ӌ(j��)ij�����I(l��ng)㕵ķ������~��ԓ����������D�ý�����(l��i)���µ��ǷN��������̫�^(gu��)�����ַ����_(d��)����־�ɳǡ����ý�����(g��u)�����L(zh��ng)����(sh��)�ֱ��F(xi��n)�r(sh��)�g���յȵȡ�
�����������f(shu��)�����ұ��C�Ƿ��`���������������_(t��i)�����˺����(m��ng)Ůʿ�Ԃ��е�һ��Ԓ������(d��ng)Ȼ�@�ӵķ����@Ȼ���Ժ�Ҋ(ji��n)֮��ԏ������ֱ�X(ju��)�w��(hu��)����Ҳ��(y��ng)�ٺ�Ҋ(ji��n)�ˡ�
������W(xu��)���ã����s���ˇ�(gu��)�cʮ����ʮ��I(xi��n)�Y���̡�������͌W(xu��)У��Ľ���ϵ������[���҂�Ҳֻ�ǿ����[������ϲ�g (t��ng)���������_(d��)�M(j��n)�DžR��(b��o)�����ĸ��ԣ����A��������õ��ˇ�(gu��)�҄�Ժ�����O(sh��)Ӌ(j��)���������Ĵ�ɤ�T(m��n)���ͼ������ȣ�Ҳ���ǂ�(g��)���һ����ɫ��������̹��߀�м��������S��(b��o)�࣬�Tλ���Ǖr(sh��)��(sh��)��Ӣ�۵Ġ�(zh��ng)Փ������(qi��ng)�֡�
������ӛ���С�ʮ�̡���߀��һ��(g��)�(xi��ng)Ŀ�c���A���P(gu��n)ϵ���찲�T(m��n)�V��(ch��ng)�|��(c��)�Ěvʷ���������^���mȻԓ���̵��O(sh��)Ӌ(j��)�������ڱ���ij���O(sh��)Ӌ(j��)Ժ������қ](m��i)Ū�e(cu��)��Ԓ�������^�����ġ���һ�O(sh��)Ӌ(j��)��;���ͷ�����������A�������˲�������˽��Ҳ�����˲�ͬ��Ҋ(ji��n)֮��(zh��ng)Փ�������������X���У���(qu��n)ֻ��(d��ng)��ӡ���ӛ����ǡ�ֺ���̹�����������P(gu��n)��
������ˣ����ڕ�(sh��)�D�в���ϣ���ķ������όW(xu��)�r(sh��)�� (t��ng)�n�Pӛ�������f(shu��)������(xi��)�µľͲ�ȫ���ؑ��ˡ�
������ʮ��ǰ���ġ��v�����͡��ﲩ��������U(ku��)����С���(gu��)�����ˣ��O(sh��)Ӌ(j��)�������Ѳ�ͬ�������f�����f(shu��)Ҳֻ�ܾ���Փ���ˡ�
����һ��(g��)���쿴��(l��i)һ��(g��)���dž�(w��n)�}�Ć�(w��n)�}���Ǖ�(hu��)���s��һ��(g��)��(w��n)�}�������ⴰ��(w��n)�}���_(k��i)���_(k��i)���Ć�(w��n)�}��
������������ͬ�W(xu��)Մ���@��(g��)��(w��n)�}�r(sh��)�������ڡ��h(hu��n)����(du��)�������Ӱ푵��}Ŀ�����x���һ��(g��)��(sh��)�����������f(shu��)�������O(sh��)Ӌ(j��)�������Ƀ�(n��i)������������(n��i)���Ă�(g��)������Ҫ�����w��r����(du��)���@��(g��)��(w��n)�}�������Ѓɂ�(g��)�O�ˣ��й������x��Ψ�����x��ֻ��(qi��ng)�{(di��o)һ���档����չ�[�^���ă�(n��i)���v������ʽ����Ҫ�����治ϣ���_(k��i)�������vʷ���������^�t��������ԭ��Q���������_(k��i)�������ÿ�������������(qi��ng)�{(di��o)�@����(g��)�֣������Ё�(l��i)�^������ijλ��Ҫ�I(l��ng)��(d��o)���f(shu��)�ģ������ڌ��҂��R��(b��o)�����r(sh��)���f(shu��)��ij��(g��)��DZ�һ�ӟo(w��)����ҕ�D��һ���Ԕ�֮��Ҳ��һ��(g��)��ͨ�ϰ����f(shu��)�ģ��f(shu��)����̫������ɣ�������ϲ�g���찲�T(m��n)�V��(ch��ng)߅�ϳ��F(xi��n)һ��(g��)���]�ķ��ӡ�Ψ����Щ֪�R(sh��)���ӌ���߀�ڪqԥ�����(sh��)��څ���΄�(sh��)�£�߀��ÁG�����^�F(xi��n)�����x����������ͼ��g(sh��)ꇵء�
�����r(sh��)���D(zhu��n)�Q������ٻ�����(d��ng)�꣬�䌍(sh��)һ�c(di��n)Ҳ����֡��ٷ��Ľ���������m�ã���(j��ng)��(j��)�����ܗl����ע�����^���@�����f(shu��)�ġ����^�����ƺ�����������ڵ�����������������ǡ�ϲ��(l��)Ҋ(ji��n)��������
�����Ҳ����������ض�Ҳ��ì�ܵġ��ă��c(di��n)����(l��i)��һ�Ǒ�(zh��n)���w��1948���ȥ��(gu��)������ӭ�ӽ���(gu��)��Ľ��O(sh��)�߳��ĴҴҷ���(gu��)������һ�w�c�T����W(xu��)��һ�ӵġ���(qi��ng)��(gu��)��(m��ng)�������Ǹĸ��_(k��i)��˼���ŭh(hu��n)���£��I(l��ng)㕾��g�͂����F(xi��n)����������Փ���о���Ͷ���˘O�����;�����
�����������x����ʲô����ͬ���ڡ�������Փ���v�n���v�oͬ�W(xu��)�����ǘӡ�
�����D(zhu��n)�۵���1960��������������o��(d��o)�n���O(sh��)Ӌ(j��)����Ժ���@�r(sh��)���˸����r(sh��)�g���|��������ͬ�W(xu��)��?c��)��ώ����I(l��ng)���{(di��o)���˶���(g��)���̈́���(ch��ng)����Ԕ��(x��)���DZ�������ˇ�g(sh��)��Ժ�v��(ch��ng)��������(ch��ng)��һ��(g��)��(d��ng)����õ�Ԓ������(ch��ng)�����������ӛ�������_(t��i)��߀�����������İ�ɫ���X(qi��n)�����ǡ����^�����һĻ�IJ���߀δ��ж���������ҹ����������������(l��i)�Ĵ��I܇(ch��)��������������һ���������b��(sh��)��һ���P(gu��n)��ؐ��ҵġ��F(xi��n)�ڻ�������(l��i)�������^�ߴ瑪(y��ng)��(d��ng)����Щ�����ġ�(���Լҕ�(sh��)�е����Z(y��))��
����Ҳ����������ׂ�(g��)ͬ�W(xu��)��Ȼ��ã��s�L��������У�@��ܰ����҂���(zh��n)�r(sh��)�����˄���Ժ��ӛ��������ǣ����δ�����һ��(g��)���P(p��n)��ɢ��ļt�����c(di��n)�Y�ˎ�ֻ�Sɫ�����棬���ߺ܌�(xi��)��(sh��)��ɫ�{(di��o)��(qi��ng)�ҡ��@����������Ԣ�����������c(di��n)���������ϣ�� (t��ng)��һЩ��Ȥ���˻����f(shu��)�o�҂����ƺ��](m��i)�У����](m��i)��ʲôӛ����������C����
�������^(gu��)�^��(l��i)���ǂ�(g��)����Ď����P(gu��n)ϵ߀�����c(di��n)�o�������������У��W(xu��)�������h���꼉(j��)��������������һ��ϵ�^�T(m��n)�d��������´��������ֈ�(b��o)���ǡ������\(y��n)��(d��ng)���нҰl(f��)��λԒ������g(sh��)�ώ��ģ����ֈ�(b��o)������ϵ���λ֪�������L��(hu��)��ֵČW(xu��)����
�����Ǵΰ��L��������ֻӛסһ��Ԓ�����f(shu��)ÿ��(l��i)�������ڿ�����Ҫ��һ�顣�҂��W(xu��)���ģ����˿��K(li��n)�ģ���Ҳ��醣���ϧֻ�ǿ����D������߀�f(shu��)����Ո(q��ng)��һ�®���(һλ���@���H�ĈD��(sh��)����T��һλ����(j��ng)������ϵ�̎����O��Ӣ�Z(y��))�������Ą�(l��)��Ҷ����⿴�����@���Dz����ˡ�
�����������ܶ��f(shu��)�������ώ��R�ء��������l(f��)��ҵ��dȤ�������Ǵ����������ң��ش��҂��Ć�(w��n)�}��
����������ô���M(j��n)�R���T(m��n)�µģ��������f(shu��)���ҽo����(xi��)��һ���U���ҵĽ����^���ţ��������ţ��ͽ������ҡ��ن�(w��n)��ʲô�����������f(shu��)����?y��n)������Ї?gu��)�ˡ�
���������������R�،W(xu��)��(x��)�ģ��������f(shu��)����?gu��)����������?/p>
�����ن�(w��n)������(d��ng)�r(sh��)һ���Ўׂ�(g��)�Ї�(gu��)�W(xu��)�����������f(shu��)��߀��һλ�؇�(gu��)��ȥ���Ͻ�С�W(xu��)ȥ�ˡ��������](m��i)�Ќ�(du��)�@λͬ�����x���ʾ���h���B�~Ҳ�](m��i)�С�
�����Ǖr(sh��)�R���x�����ã���(gu��)�H�����硢ˇ�g(sh��)����Z��(d��ng)���҂��@���Ĭ���҂��](m��i)�І�(w��n)�c�����P(gu��n)�Ć�(w��n)�}��
�����҂����I(y��)�ˣ��xУ�ˡ����Î������Զ�̎�����L(zh��ng)�Ą�(d��ng)�y�С��ٺ�����Ҋ(ji��n)�棬���ǽٺ������1970�������������Ҋ(ji��n)���������ώ�һ�����ӵأ��ڽ������ؽ����r(n��ng)�����ٽ��������@�ģ��������f(shu��)Ԓ������ô�֓P(y��ng)�D�졭��
�������D(zhu��n)�^(gu��)ʮ�꣬�LJ�(gu��)�ҵ�������Ҳ������̹�����@�ӵ��όW(xu��)�˵������� (t��ng)�f(shu��)������æµ����(l��i)������(gu��)�⽨���W(xu��)����Փ����(sh��)�����ڴTʿ����ʿ������
�����Ҽ��Ľ����I(y��)�W(xu��)Ժ��Ո(q��ng)��̹������(l��i)У�v���F(xi��n)�������W(xu��)��ABC���F(xi��n)�������Ę�(g��u)�D����Ҳ���ڽ���������o (t��ng)���·��ֻص������p�r(sh��)��������Ȼһϯ��ǻ���{(di��o)�����f����һ�B��Ƭ���f(shu��)���d�^̎���w�������ƺ�������Ÿ������h(yu��n)������2013.2
����ע������ǰ�f��һ�������F������ӆ����������һ��������ꎡ��䌍(sh��)����W(xu��)�����ң����p�����£�֪����Ҳ�Hһ����Ҳ�����F�У��������Ҿ����ˡ�2014.1

���ij������P(gu��n)ע�ij����W(w��ng)��
<sup id="ecicy"></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