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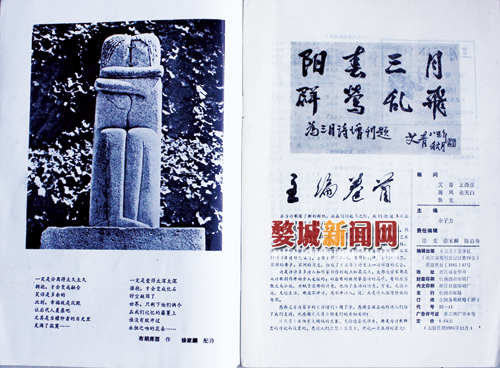
金華《三月》最早提出微型小說概念
徐家麟是嘉興人,他自小對文學創(chuàng)作存在一股天然的沖勁。在初中的時候,恰逢大躍進時期,他已經(jīng)熟諳民謠的風格,向當時浙江省文聯(lián)主辦的《東海》投稿,可惜石沉大海,毫無音訊,這并沒有使他氣餒。讀大學時,他是班上的黑板報能手,一直到文革結束,他都沒有絲毫松懈。直到林彪事件,他下放的軍墾農(nóng)場也受到波及,以致在安排他們的工作時,他挑選了金華。徐家麟說,“因為當時留在嘉興的人比較多,何況金華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也比較好。”
初到金華時,他被分配到金華化肥廠工作。1982年春天,他進了當時的《金華日報》,接觸到同一個印刷廠印制的《三月》雜志。徐斐作為《三月》的編輯,在印刷廠跟徐家麟多有交流,甚至有所請益,以致1984年文學風潮高漲時,《三月》正式向全國發(fā)行,宣傳部把徐家麟調往《三月》工作,他由于自己喜好文學創(chuàng)作,二話沒說就去了。據(jù)他所說,《三月》雜志的初期,僅有主編余子力以及他和徐斐兩名編輯。《三月》的核心也就是他們?nèi){馬車拉著跑。他們率先在全國打出“微型小說”的概念,為了抗衡當時已經(jīng)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十月》、《收獲》等雜志,之后,在《三月》停刊以后,“微型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為鄭州的《小小說選刊》所重用,直至他們改刊為《微型小說選刊》,金華失去了一塊文學招牌,甚過對王柏等北山學派的漠視。
《三月》雜志的社址從借用群藝館的房間到租用軍分區(qū)招待所旁邊的小屋,一路坎坷顛簸,卻又充滿理想主義色彩,金華文學自十年動亂以后的復蘇,幾乎都可以在《三月》這本純文學雜志上得以體現(xiàn)。徐家麟說,“從《三月》走出來的金華小說家有葉玲、蔣啟倩、陳武,詩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但自從《三月》停刊以來,這些文學愛好者都銷聲匿跡,轉戰(zhàn)他場。
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當《三月》雜志接到通知,他們將和溫州的《文學青年》一樣不再允許發(fā)行時,這一切都注定了文學的衰落。當時,茍延殘喘的雜志不外乎《東海》等老雜志,地方性刊物因為一紙文件,所謂省級以下地市級城市基本不辦文學雜志,一應取締。盡管《三月》在最好的時候能夠全國發(fā)行五六萬份,吸引了大批文學青年的投稿,作為《三月》主編的余子力甚至當時的宣傳部長也曾竭力爭取,然有心無力,為政策所阻。
“我們?yōu)榱死硐攵陝樱裉靺s是一片迷茫”
徐家麟對于時代的轉換確實有一種未覺先知的認識,從小喜好文學的他,并沒有選擇中文系,而是走了有機化學的路子。他說,“兩三年就進行一次政治運動,搞文學的還不是首當其沖。”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對當時的一種猜想上面——“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塑料的世界”,沒想到數(shù)十年之后,這已經(jīng)不是一個猜想,乃至他所崇尚的文學,也幾乎成了一個“塑料的文學”。
談論80年代,他比李陀他們所編選的《八十年代回憶錄》更樸實些,對于熊召政的一首《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仍有鮮明的印象。熊召政以此聞名全國,盡管他的為人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充滿非議,至今仍讓他自己諱莫如深。1989年,徐家麟編了一本名為《青春的躁動》的詩選,他在一首《〈三月〉的故事》中寫到,“一切都已過去了,那些春光和風雨交織的日子,當初夏的腳手架輕輕拆下,《三月》,已凝成雕塑。八個春秋的辛勤雕刻,終于在江邊崛起,升華為藝術的美麗;自豪地讓人們留戀。三月是美好的,這是艾青的歡呼,而她躁動的刊名,是時代的賦予。歲月會沉淀混濁,只剩下潔白,一百年后,人們來到這里,還會講一個《三月》的故事。”
近三十年的文學匱乏期過后,人們對文學的需求遠遠超過了生理需求。以致徐家麟說,“那是一個文學神話的時期,也是一個文學非常崇高的時代。”與今天的世俗社會幾乎構成了一個相反的景象。一切被文革時期破壞到不能更壞的地步,以致文學的春天只能向著更深遠的未來。
在徐家麟看來,所謂的現(xiàn)代詩僅僅來自他自身的生命沖動,除了課本上僅有的古詩詞,他并沒有受到現(xiàn)代詩潮的任何影響,他是直接來源于自身的直覺而沒有額外的接觸,以致從文革以來,朦朧詩這一旗幟下,他或許是金華最早嘗試朦朧滋味的詩人。在他的詩集《昨天的歌》中,他把出浴的女人比作一支白蠟燭,堪比象征派初期的法國詩人們。作為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獻禮,青春的躁動在三十年前與今天形成了一個反向,徐家麟說,“我們的躁動是為了理想,然而今天的浮躁卻是一片迷茫。”

看婺城新聞,關注婺城新聞網(wǎng)微信
<sup id="ecicy"></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