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 id="ecicy"></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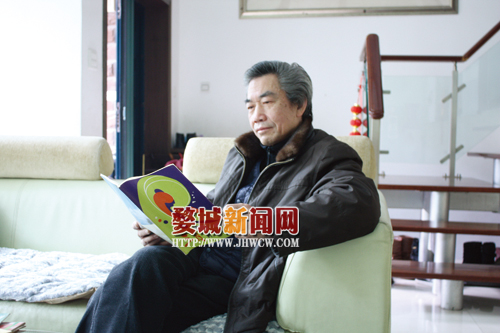
“深化文化改革并非只為了利益”
徐家麟在《三月》工作的歲月,基本上經歷了《三月》的輝煌和幻滅,這是一個充滿苦樂與辛酸的階段,對他來說,或許一切意味著我們擁有一場過于龐大的記憶需要在今后作為陳述的資本。在1986年,《三月》甚至給全國的文學青年進行文學函授,寄發有關文學創作的理論資料,并且在雜志上開辟專欄用以點評他們的作品。
當《三月》停刊以后,金華就失去了文學園地,即便在2000年以后網絡盛行,作為全國知名的金華詩歌論壇——四季詩歌論壇乃至荒誕派詩歌在金華崛起的時候,也無法比擬當年《三月》在金華的影響。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瞬間就被淘干凈了,剩下的只有無盡的緬懷和忘卻的紀念。作為新一代的人們,對于《三月》幾乎根本不知道底細,就像他們對于文學根本不辨東西而一味地屈從于所謂的媒體宣傳。浮躁的時代,并沒有讓我們看清浮在表面的究竟是什么,但躁動的青春卻是一片虛無。
徐家麟說,早春二月,即便有反復,也讓人知道春天來了。就像雪萊說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么”。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已經使人們忘記了傳統文化,徐家麟說:“我們提倡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并非純粹只是為了經濟利益。”
顧工、顧城父子也曾給《三月》投稿
教育的失敗,或許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大的失敗。西蒙娜·薇依說,“有‘根’也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也最未被認識到的需要”,然而我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終于成為漂泊者,“房屋已成過去……現在最好的辦法是把這些東西當作過期罐頭扔掉……”,阿多諾不必多說,我們已經領會他所說的精髓。當時下海經商成為迫切想擺脫貧困的人們的首選,萬元戶一時成為人人羨慕的對象。因此,《三月》的停刊似乎只是一個象征,因為全國的文學刊物幾乎在同一時期面臨著萎縮的命運。
菲羅斯特拉托斯說,“諸神感知未來的事情,凡人感知現在的事情,但是智者感知即將發生的事情。”我們明明知道發生了什么,但發生的一切又使我們趨向遺忘。所以丁玲寫給《三月》的寄語,興許是頗為中肯的,“希望微型文學的投稿人,也要多讀些馬列主義和其它社會科學書籍,向人民學習,才能認識社會……寫出真正反映時代、推動歷史前進的文學作品。”那么,特里·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里面所說的“的確,精神是超脫世俗的東西,但并非是牧師構想的那種。眼下的這個世界已經流為陳俗,而社會主義者必將構建一個全新的世界取而代之。如果你不能從這個意義上超越世俗,那就意味著你需要仔細審視一下你周圍的世界了”是否依然有效?
或許我們一直能夠看懂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女士為《三月》題寫的“團結,奮斗,建設祖國”這樣簡易的話語,直到今天,因為時隔塵囂,朦朧詩的天才詩人顧城曾在《三月》上發表的詩作,能夠引起的驚詫也僅僅是有限的幾個人,這在當年文學刊物云集的中國算不上什么事兒,可我們仍然看重這樣的收獲。顧城和他父親顧工在《三月詩增刊》上的詩作,一如他在《一代人》中所寫“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對徐家麟來說,文學絕不是一個人可以戰斗下去的,當徐斐離開了《三月》,他也無法堅守一個人的陣地。也許這一切在他想來是一個很可惋惜的事情,金華從此再也沒有一本刊物可以在全國發行,似乎也不再有這種可能。即便他懷有這樣一個夢想,“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也有咫尺天涯的感慨。他在1989年《三月》停刊以后,轉到金華電視臺工作,一直到15年后退休為止,文學仍是個夢,至今不曾醒來,就像飛碟一樣,他未曾親眼目睹在金華上空掠過。顧城在他的詩中寫到“是有世界,有一面能出入的鏡子,你從這邊走向那邊,你避開了我的一生”,這一切如他的詩題一樣“我承認”,我承認并沒有勝利可言,也不至于一敗涂地,似乎還有翻盤的余地,但艱辛的旅程幾乎都留給了我們身后的人。

看婺城新聞,關注婺城新聞網微信
<sup id="ecicy"></sup>